在费格森和巴尔的摩,城市暴动为什么会发生? - 彭博社
Fola Akinnibi
 抗议者在2015年弗雷迪·格雷在警方拘留中去世后聚集在巴尔的摩市政厅。
抗议者在2015年弗雷迪·格雷在警方拘留中去世后聚集在巴尔的摩市政厅。
摄影师:帕特里克·史密斯/盖蒂图片社北美1954年,当第一批家庭搬入位于圣路易斯北部的普鲁伊特-伊戈住房项目时,这本应开启城市更新的新纪元。像美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该市拆除了黑人低收入和工人阶级社区,以为这个由建筑师山崎实(后来因原世贸中心而闻名)设计的33座塔楼的公共住房综合体腾出空间,旨在容纳超过10,000名被迫迁移的居民。但普鲁伊特-伊戈很快就变成了严重隔离和极端投资不足的地方,而不是新现代主义塔楼中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到1960年代末,只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占用,高层综合体处于失修状态。1972年,联邦政府在直播电视上用炸药拆除了三座塔楼;其余的几年前也被拆除。这场为期二十年的实验被认为是失败,并被视为联邦公共住房努力的污点。
 1971年圣路易斯的普鲁伊特-艾戈住宅项目。开业不到二十年,综合体内大多数建筑已空置。摄影师: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拆除使圣路易斯处于另一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前沿。到1990年代,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正在资助全国各地公共住房塔楼的拆除,理由是这些地方是集中贫困的口袋,滋生犯罪和混乱。居民们将再次被迫迁移,这一次,许多人被迁离城市中心,因为城市希望收回空间以供高收入居民和企业使用。
1971年圣路易斯的普鲁伊特-艾戈住宅项目。开业不到二十年,综合体内大多数建筑已空置。摄影师: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拆除使圣路易斯处于另一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前沿。到1990年代,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正在资助全国各地公共住房塔楼的拆除,理由是这些地方是集中贫困的口袋,滋生犯罪和混乱。居民们将再次被迫迁移,这一次,许多人被迁离城市中心,因为城市希望收回空间以供高收入居民和企业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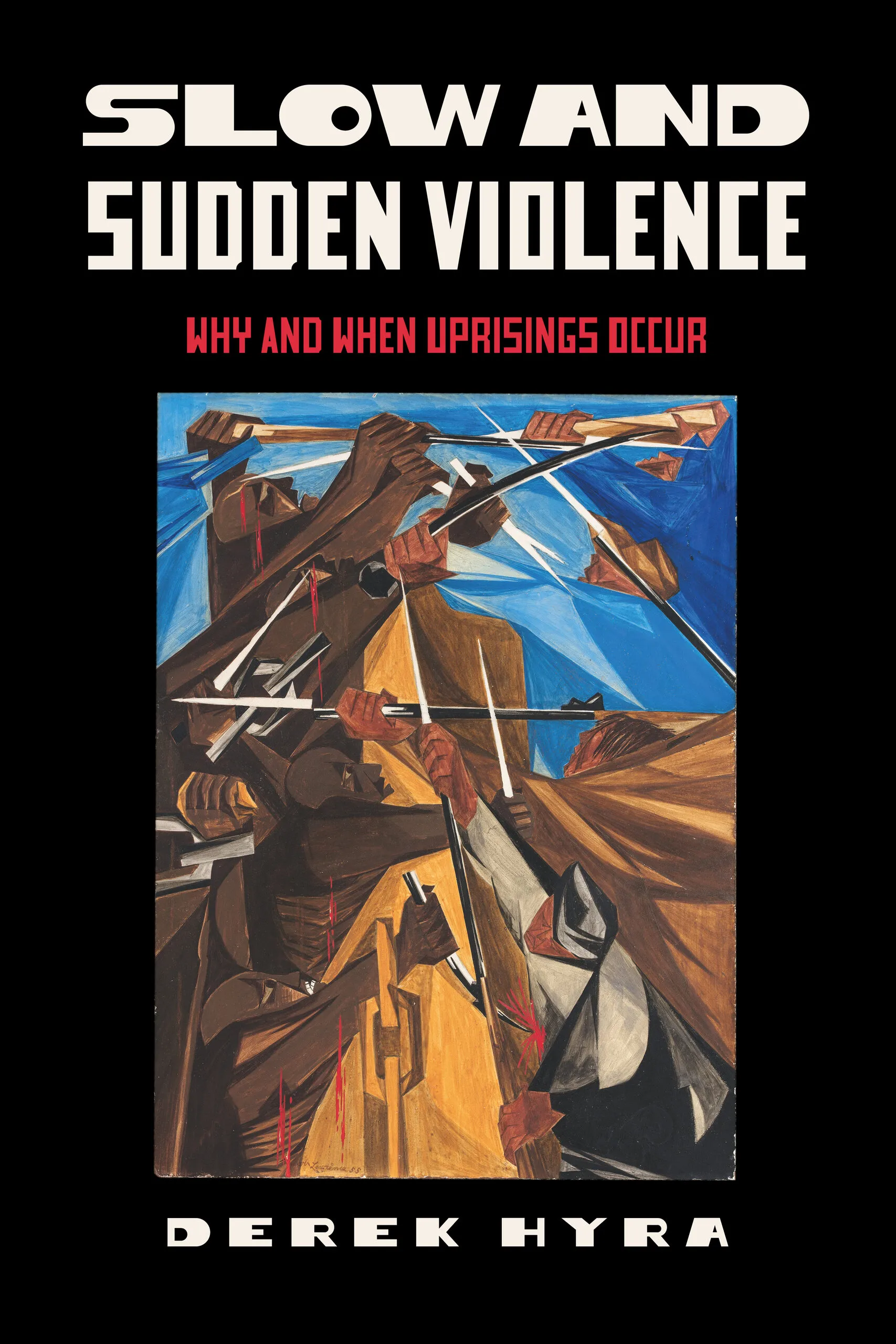 来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这种破坏和流离失所的循环是一种暴力形式,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公共管理与政策教授德里克·海拉(Derek Hyra)表示。在他的新书中,缓慢与突发的暴力,海拉将历史城市更新政策与现代城市暴动联系起来。海拉表示,他希望为2014年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杀害迈克尔·布朗和2015年在西巴尔的摩的桑镇社区杀害弗雷迪·格雷后爆发的挫败感和愤怒提供背景。
来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这种破坏和流离失所的循环是一种暴力形式,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公共管理与政策教授德里克·海拉(Derek Hyra)表示。在他的新书中,缓慢与突发的暴力,海拉将历史城市更新政策与现代城市暴动联系起来。海拉表示,他希望为2014年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杀害迈克尔·布朗和2015年在西巴尔的摩的桑镇社区杀害弗雷迪·格雷后爆发的挫败感和愤怒提供背景。
“我的直觉是还有其他暴力,”他说。“我想尝试将发生的城市重组和90年代、2000年代的流离失所与我们所看到的激进警务联系起来。”
彭博城市实验室与Hyra讨论了他的书以及有助于解释为何会发生暴动的城市政策背景。对话经过编辑以便于长度和清晰度。**这本书的想法来自哪里?**我主要研究的是绅士化和再开发,以及如何进行公平发展。我从未真正关注过暴动和动乱以及黑人反抗。当我完成 我的最后一本书时,2014年发生了事情,弗格森点燃了。然后在2015年,巴尔的摩发生了 弗雷迪·格雷的死亡事件。正是在我看到 CVS在Sandtown被烧的那一刻,我说:“我必须投入其中。”当我去弗格森和Sandtown时,我只是问人们与暴动的潜流有什么关系。当然,人们提到了警察的侵略性。但人们也开始谈论他们的家庭历史。这有助于为他们在弗格森或Sandtown的处境提供背景和解释。他们告诉我其他政策机制如何推动巴尔的摩或圣路易斯地区的贫困,这也与他们的挫败感有关。
**似乎争论的焦点是现代城市发展是暴力的吗?**是的。讽刺的是,一些人创造的工具是为了应对隔离。我们在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建起了高楼,这导致了一个隔离的都市环境。那么在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拆掉它们。很多人认为拆除公共住房高楼是对人们最好的选择,因为生活在集中贫困中是困难的,限制了生活机会。但我认为我们这样做的方式并没有缓解贫困。它只是推动了贫困。它进一步将贫困重新隔离到我们的中央商务区之外,并打开了靠近市中心的社区进行绅士化。
拆除公共住房,尽管有着良好的意图,但实际上是暴力的,并使许多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人们得到了 第8节券。这些租金补贴在哪里被接受?在低需求住房社区。贫困就集中在像东南费格森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使用其他政策,比如 税收增量融资,那么谁从中受益呢?好吧,它投资于曾经有公共住房的社区。现在公共住房消失了,社区开始绅士化,我们有高收入人群搬入由税收增量融资促进和刺激的便利设施。
**这场反抗与那种暴力有关吗?一个跟随另一个吗?**高楼倒下,然后新的墙壁竖起。警察监督的墙壁。在这些社区中,基于种族和空间压迫的循环,愈演愈烈的挫败感。人们在被迫迁移时,只能继续生活,生活在集中贫困中。当暴力的警察杀戮发生时,它释放了日益增长的挫败感。
 2014年11月29日在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坎菲尔德公寓前的示威。摄影师:埃里克·泰尔/华盛顿邮报通过盖蒂图片社我试图将缓慢的政策暴力与贫困的集中联系起来,然后是警务的突然暴力。当你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这就是动乱的配方。我们国家的对话确实集中在警察暴力上。我们正在尝试改革警务,但我们对慢性贫民区做了什么?我们是否投资于黑人和棕色社区?我们是否停止或减缓了城市更新?我们是否最小化了黑人迁移?我认为没有。
2014年11月29日在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坎菲尔德公寓前的示威。摄影师:埃里克·泰尔/华盛顿邮报通过盖蒂图片社我试图将缓慢的政策暴力与贫困的集中联系起来,然后是警务的突然暴力。当你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这就是动乱的配方。我们国家的对话确实集中在警察暴力上。我们正在尝试改革警务,但我们对慢性贫民区做了什么?我们是否投资于黑人和棕色社区?我们是否停止或减缓了城市更新?我们是否最小化了黑人迁移?我认为没有。
**政策制定者如何打破这些循环?**利用税收增量融资来刺激服务不足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与可负担住房政策相结合。我们必须将对话从城市更新转向公平发展。公平发展是指以最小化迁移的方式投资于低收入的黑人和棕色社区。不要拆除公共住房——保护公共住房,同时引入高收入人群。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城市领导者和联邦政策制定者考虑如何以公平的方式进行投资。
我们需要应对不平等的政策,而地方领导者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拥有来自联邦政府的强大社会安全网,而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安全网。当你查看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的预算、可负担住房的预算、社区经济发展时——进入市政当局的资金并不足够。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联邦层面进行政治海啸式的变革,以进行更大的投资,最终将其转移到地方层面。但我也认为地方领导者必须承担政治风险。**有没有你看到的市政当局或地方,即使是小规模的,做得对的地方?**有一些元素。波特兰经历了动乱和骚乱。他们已经推出了 可负担住房的债券。我认为市政当局必须考虑长期;他们必须引入额外的资源。我们为建设学校、图书馆和游泳池推出债券公投,但有多少市政当局推出长期债券来提供可负担住房?并不多。华盛顿特区是另一个经历了大量城市更新的地方,但那里[市长]穆里尔·鲍泽创建了一个示范项目,实际上 帮助小企业获得房地产。当城市更新发生时,不仅仅是居民的迁移,还有商业迁移,位于城市更新地区的小型家庭企业也需要地方或联邦政府的帮助。**话虽如此,这似乎又在发生。有没有人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确实似乎这些发展和迁移的力量不断发生。[弗格森和巴尔的摩]似乎在重复导致他们最初发生骚乱的周期。如果我们不解决慢性迁移创伤,我们将再次发生骚乱。除非我们进行必要的公平发展,否则今天会有骚乱,明天会有骚乱,永远会有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