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 Life Startup Kift在国家公园推广远程工作 - 彭博社
Ellen Hu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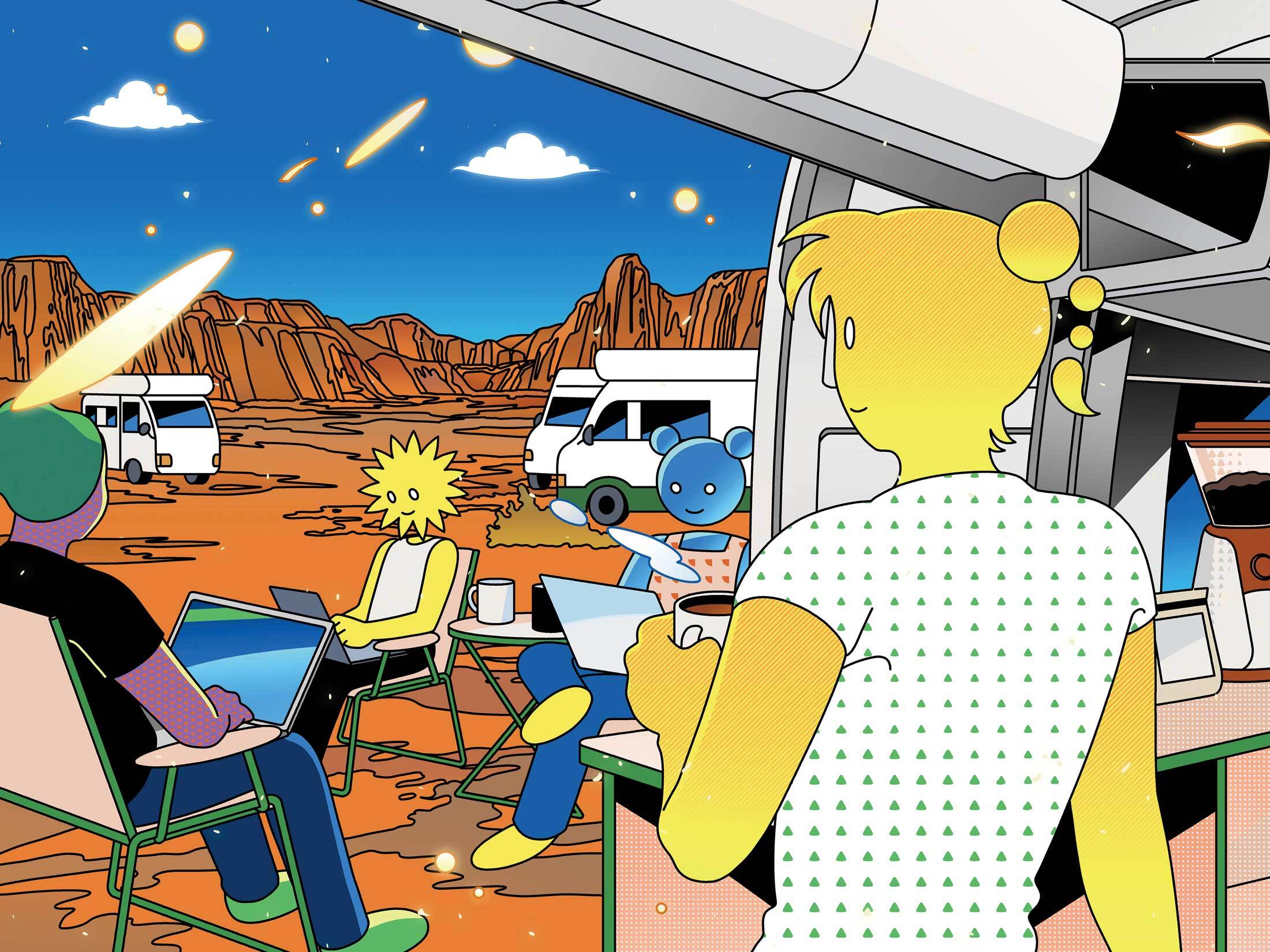 插图:Jinhwa Jan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插图:Jinhwa Jan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公寓大楼,于2月13日。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公寓大楼,于2月13日。
摄影师:Krisztian Bocsi/Bloomberg我刚好赶到“车居生活”公社参加团体冥想活动。其他大约20多名冥想者——大多是忠实的车居者,还有一些只是来参观的好奇者——已经躺在混凝土露台上闭着眼睛做瑜伽尸体式,所以我受到欢迎,被安静地嘘寒问暖,并被引导到角落的毯子上。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约书亚树的一个星期六下午4:30,距离以其拟人化的丝兰植物而闻名的国家公园只有15分钟车程,温暖的沙漠风吹动着一块遮阳帆,脸上沾满了沙子。
我们的主持人告诉我们想象一个金光闪闪的球在我们的身体中穿行,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敲响了一小群铃、风铃和水晶钵。两只自由活动的宠物狗四处嗅探,而第三只则在某人的手机闹钟声中打呼噜。当最后一声钟声停止响起时,每个人都迁移到了房产内的两卧室房屋,里面有一个相当豪华的厨房,一起做晚餐。我们围着餐桌手牵手,感恩这顿饭:烤甜椒、无麸质意大利面、葵花籽酱。然后,夜幕降临,房子变得漆黑。居民们走出去在各自的房车里睡觉,这些房车停放成一个松散的圆圈,就像俄勒冈小道上的一群有顶篷的马车。
如果这个场景听起来更像是田园诗般的,而不是噩梦般的,那么你可能是 Kift 公司 的理想客户,这家初创公司销售一种非常时尚的 Airbnb、 WeWork 和 共居 的混合产品。会员每月可以花费925美元(或者年度计划每月425美元,对于需要的人有更低的滑动价格),将他们的货车带到公司的四个复合物之一,公司称之为俱乐部。他们还可以从公司租用翻新的梅赛德斯-奔驰 Sprinter 货车,每月额外花费2500美元。从功能上讲,这些地点是带有更好品牌、更友好邻居和更豪华设施的房车公园。与其独自旅行,每晚寻找互联网和一个平坦的停车地点不同,大约25名旅行者组成的团体在一个固定建筑物周围生活约一个月。每个设置都有一个厨房、长桌用于笔记本电脑工作和电话会议、快速无线网络,正如网站承诺的那样,“共享价值观、健康生活方式,以及探索工作、庆祝、创造、分享故事,一起笑和哭。”
我拜访的团体是第二批 Kift 学员,一旦他们在约书亚树的时间结束,他们就开着货车前往下一个临时住所,距离300英里之遥的亚利桑那州阿科桑蒂。之后,一些成员绕道前往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然后在加利福尼亚州莱克波特的另一个 Kift 地点重新聚集。一旦车队结束,一些人踏上新的冒险之旅,而另一些人则留在莱克波特。在两个阵营中,都有很多讨论在另一个俱乐部见面。未来聚会的提议包括西部美国其他具有品牌抱负的目的地,包括华盛顿州的发现湾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
 在白天,Kift俱乐部变成了临时工作空间的海洋。摄影师:Annie Tritt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在约书亚树,坐在桌子前的那个人是Kift的首席执行官Colin O’Donnell。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他的聚会不仅仅是一个答案,而是解决住房不可负担性、企业贪婪、气候变化和孤独的答案。他不是在针对退休人士的房车,也不仅仅限制在已经在路上过着vanlife的游牧民族。他希望说服越来越多有幸可以全职远程工作的白领美国人,放弃他们的固定、孤立的家,尝试与志同道合的旅行者共同生活。“我们过去整天都是和同事坐在一起,和朋友在线聊天,” O’Donnell喜欢说。“现在我们整天和朋友在一起,在网上和同事聊天。感觉更好一些。”
在白天,Kift俱乐部变成了临时工作空间的海洋。摄影师:Annie Tritt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在约书亚树,坐在桌子前的那个人是Kift的首席执行官Colin O’Donnell。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他的聚会不仅仅是一个答案,而是解决住房不可负担性、企业贪婪、气候变化和孤独的答案。他不是在针对退休人士的房车,也不仅仅限制在已经在路上过着vanlife的游牧民族。他希望说服越来越多有幸可以全职远程工作的白领美国人,放弃他们的固定、孤立的家,尝试与志同道合的旅行者共同生活。“我们过去整天都是和同事坐在一起,和朋友在线聊天,” O’Donnell喜欢说。“现在我们整天和朋友在一起,在网上和同事聊天。感觉更好一些。”
O’Donnell于2019年开始建立Kift,但疫情赋予他的初创企业一支突然脱离办公室的劳动力。Instagram的幻想迅速变成了人生计划。根据咨询公司MBO Partners的数据,现在有超过1500万美国人自称为“数字游牧民”,而疫情前这个数字约为700万。Airbnb上长期预订的每九个人中就有一个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描述为游牧,而Airbnb公司宣布其6000多名员工永远不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些价值5万美元的Sprinter房车已经被预订了几个月,整体美国房车销量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
在硅谷,公司喜欢滥用时髦词汇,但 Kift 几乎同时使用了所有这些词汇
在所有利用这种漫游热潮的公司中,Kift 的修辞最为高远。它不仅仅是租给你一辆货车,而是试图让你转变为一种强调分享事物的颠倒生活方式,包括梦想和感情。我在约书亚树遇到的 Kift 居民年龄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等,包括一位创业者、一位软件工程师、一位元宇宙营销人员、一位创意机构设计师、两位项目经理、一位戒毒辅导员和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们信奉奥唐奈对技术嬉皮复兴的愿景,这得益于卫星互联网和 Zoom 的可能性。Kift 承诺,它的社区意识可以弥补在路上生活中可能带来的额外孤独感。哦,它的社区意识还包括专门的加密货币代币,不受最近加密货币崩盘的影响。
在硅谷,公司喜欢滥用时髦词汇,但 Kift 几乎同时使用了所有这些词汇。这是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城市,共同生活,自动和电动车辆,再加上一点区块链的调味。然而,如果你能克服想要翻白眼的冲动,你可能会看到美国初创企业文化的一条更健康的道路,这种文化在看似无底的风险投资中醉生梦死了十多年,现在面临市场崩溃,迫使它戒酒。奥唐奈和他的一些同行正在拒绝现金篝火和庆祝一切成本增长模式,而是直接从客户那里筹集资金。
奥唐奈和他的同伴们所拥有的是这一刻,这比过去一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适合他们的推销。没有人真的确定未来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但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现在拥有的糟糕透顶,需要改变。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的新方式时,为什么不带上我们的家人和一些友好的熟人一起前行呢?
 奥唐奈在40多岁时从纽约搬到旧金山湾区后,开始喜欢共同生活。摄影师:安妮·特里特,彭博商业周刊奥唐奈现年47岁,身材瘦削,穿着全黑,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纹身,包括左手掌上的眼球。在约书亚树的一个炎热早晨,当我们准备开车进入公园远足时,他拿起一把剪刀,把他穿的破烂牛仔裤剪成了短裤。(他在一次攀岩和徒步之间的岩石攀爬中撕破了这条裤子。)然而,十年前,他还是纽约市一个穿着正装的企业科技人员。
奥唐奈在40多岁时从纽约搬到旧金山湾区后,开始喜欢共同生活。摄影师:安妮·特里特,彭博商业周刊奥唐奈现年47岁,身材瘦削,穿着全黑,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纹身,包括左手掌上的眼球。在约书亚树的一个炎热早晨,当我们准备开车进入公园远足时,他拿起一把剪刀,把他穿的破烂牛仔裤剪成了短裤。(他在一次攀岩和徒步之间的岩石攀爬中撕破了这条裤子。)然而,十年前,他还是纽约市一个穿着正装的企业科技人员。
奥唐奈童年混乱,几乎没有高中毕业,大学辍学。20多岁时,他有了两个孩子,急切地需要证明自己。他负责监督LinkNYC项目,该项目于2015年开始将纽约市的电话亭改造为免费Wi-Fi热点,配有大屏幕和摄像头。LinkNYC因专注于纽约最富裕的邮政编码区域和有点诡异而备受批评——它通过向路人展示根据时间、天气、地铁延误和附近商店的销售情况定制的广告来赚钱。后来,奥唐奈参与了Sidewalk Labs项目,这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 Inc.的城市设计部门,也因其广告丰富的城市设计理念而备受批评。
谁自称为“数字游牧民”?
来源:2021年7月进行的对6240名美国人的MBO Partners调查
当我们在徒步旅行中穿越沙漠,寻找薄薄的、像约书亚树一样形状的阴凉时,奥唐奈告诉我,大约三年前,他的孩子们高中毕业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越来越着迷于研究人们如何共同生活。他没有上人类学课程,而是搬到了旧金山的米申区(Mission District)的一个名为Agape的共同居住房屋,那里住着大约14个人。(他的妻子留在了原地,两人保持着幸福的非传统婚姻。)他还第一次参加了火人节(Burning Man)。
Agape是旧金山湾区共同居住场景中较为知名的房屋之一,倡导与朋友一起生活在“有意识的社区”中,通常是年轻、无牵挂的专业人士。在许多共同居住房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但居民们共同出钱购买食品,一起做饭吃饭,并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解决洗碗或招募室友等方面的冲突。许多这样的公社构成了一个与科技行业不可避免地重叠的创意人士的地下派对场景。任务管理软件公司Asana的联合创始人贾斯汀·罗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在Agape住了八年。(我也在旧金山的一个类似房屋中住了五年。)
奥唐奈带着健康的东海岸讽刺精神来到Agape,但在与那些谨慎选择措辞并倾向于给予彼此怀疑的室友们相处几个月后,他的感受和行为开始改变。“我内化并采用了我认为荒谬的语言,”他说。“我意识到当我在投射意图时,并开始理解我如何体验世界是我自己建构的。”他开始将自己以前的方式称为“纽约竞争性创伤”,并质疑为什么他曾认为更多的数据收集会导致更好的城市。
他决定他想要攀登一把不同的梯子。他看着他的室友们如何培养了一个扩展的社区,他们如何融合了友谊和家庭的概念。一天晚上,他们用手在他的肋骨上一针一针地蘸墨水刺上了“AGAPE”这个纹身。“这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奥唐奈说。
 加利福尼亚州莱克波特基夫俱乐部停车场的景色。摄影师:安妮·特里特,彭博商业周刊奥唐奈并不是第一个向科技人士推销共同生活的企业家。在2010年代中期,Zappos.com Inc.的已故联合创始人托尼·谢伊住在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的拖车公园,与他的朋友们住在一起,鼓励他所称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与此同时,雄心勃勃的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试图商业化共同生活。 WeWork Inc.推出了 WeLive,而Ollie、Common和Starcity都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成人宿舍版本,租户愿意为接近他人付费。
加利福尼亚州莱克波特基夫俱乐部停车场的景色。摄影师:安妮·特里特,彭博商业周刊奥唐奈并不是第一个向科技人士推销共同生活的企业家。在2010年代中期,Zappos.com Inc.的已故联合创始人托尼·谢伊住在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的拖车公园,与他的朋友们住在一起,鼓励他所称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与此同时,雄心勃勃的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试图商业化共同生活。 WeWork Inc.推出了 WeLive,而Ollie、Common和Starcity都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成人宿舍版本,租户愿意为接近他人付费。
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像Agape这样的公社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相继失败或被吞并,只有Common还在。教训是建立社区需要所有各方的努力,而不仅仅是一笔固定费用和偶尔的欢乐时光。“当你销售一个应该易于使用、灵活和方便的服务时,它会吸引那些想要支付账单并让一切都搞定的客户类型,”现在为Kift工作的Starcity的联合创始人莫·萨克拉尼说。Common的首席执行官布拉德·哈格里夫斯将Agape所代表的家庭称为一种怀旧的名字:“有机共同生活”。
O’Donnell说他认为他在共同生活中的经历将使他能够建立一个更像Agape的企业。在确定了面包车概念之后,他将其称为Kibbo,这是对1920年代英国露营社团Kibbo Kift的一个参考,然后将名称更改为Kift,以避免与另一家公司混淆。他在第一个大流行夏季期间推出了该公司,并得到了Burning Man首席执行官Marian Goodell的认可,然后由于Covid-19继续使他的计划复杂化,这家初创公司停滞了大约一年。与此同时,Kift成立了一个Discord服务器,感兴趣的人可以在那里互相了解。
2021年中期,随着美国的Covid疫苗更加丰富,Kift开始筹划其首次线下聚会。这次车队从纳帕谷北部出发,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漫游到莫哈韦沙漠。其想法是最终拥有一批年度会员,他们可以在少数几个俱乐部之一随时进出,以及支付几个月费用的短期会员。
 Noami Grevemberg是一位作家、播客和活动家,也为Kift提供咨询。摄影师:Annie Tritt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O’Donnell总是看到星星在对齐:远程工作、卫星互联网,也许是电动或自动驾驶面包车。有时,他会陷入一种堪比前WeWork首席执行官亚当·纽曼的夸大水平。“经济引擎已经远离了城市中心,”他说。“一个城市不再是地理上定义的。”
Noami Grevemberg是一位作家、播客和活动家,也为Kift提供咨询。摄影师:Annie Tritt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O’Donnell总是看到星星在对齐:远程工作、卫星互联网,也许是电动或自动驾驶面包车。有时,他会陷入一种堪比前WeWork首席执行官亚当·纽曼的夸大水平。“经济引擎已经远离了城市中心,”他说。“一个城市不再是地理上定义的。”
Kift 正在尝试成为一种新型创业公司,但它也在执行经典的硅谷举动:为新受众重新包装旧产品。2017年, Lyft 公司因推出 Lyft 班车而遭到广泛嘲笑,这是一项沿着预定路线行驶并定期停靠以接送乘客的大型汽车服务——就像,你知道的,一辆公交车。在 Kift 的情况下,美国露营协会已经存在了60年,人们在那之前就一直在车里生活。O’Donnell 要卖的重要部分是共同居住者和相对奢华的完美结合。他的社区是基于他们渴望旅行的愿望,当然也基于他们的特权和可支配收入而自我选择的。
在 Kift 推出时,一位记者在 Twitter 上开玩笑说,它的创造者可能会自言自语地说,“这就像一个拖车公园…但不是为那些人。”当时一位New York Times的记者问 O’Donnell,Kift 的概念是否带有反乌托邦的味道。他告诉她说,“反乌托邦和乌托邦是近亲,” 他说,区别在于选择的自由。
当我抵达约书亚树时,Kift 团队已经建立了一种节奏。公共厨房每天早晨都有咖啡,有时 O’Donnell 会制作一批冰沙。每天早上8点,居民们举行半小时的签到会议,分享他们的感受和当天的通知(垃圾需要清理,稍后会有徒步旅行),然后散开去敲击笔记本电脑或接 Zoom 电话。一些人在房子的两间卧室之一设置了显示器,这些卧室已经改建成共享办公空间。大多数人在那里或在他们的货车里接电话。
为了让新的游牧民更舒适地生活在面包车里,这个地方还设有一组户外淋浴和一个带有几个厕所的独立浴室。下午,法国电子商务设计师乔伊·里帕特(Joy Ripart)自愿教授瑜伽课,或者科技工作者大卫·克纳普(David Knapp)进行塔巴塔训练课程。每个人都在厨房的白板上报名参加晚餐烹饪轮班。所有的餐点都是由植物制成,杂货是在线订购送货上门的。团队计划在国家公园进行日出徒步旅行,并为下午的冰浴冻结了加仑大小的冰块。在那个星期一的每周家庭会议晚餐上,奥唐奈(O’Donnell)带领团队进行“清理”,这是他在阿加佩学到的一个框架,用于表达小的不满而不进行指责。在我参加的那次会议上,有人说他们担心成员可能会因为想吃肉或奶制品而感到受到评判。
 马泰·布莱克洛克(Matai Blacklock)在莱克波特俱乐部的露台上开会。摄影师:安妮·特里特(Annie Tritt)为彭博商业周刊拍摄整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既像工作又像夏令营。与会者并不是选择了彼此,但他们也有点选择了。此外,自然的壮丽景色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夜晚,团队在远离房子的热水浴缸下星空下聚会,周围是沙漠灌木。太黑暗了,看不清面孔,这让交换那些永远不会出现在Instagram上的轶事变得更容易,包括如何回答朋友和初次约会时关于 #vanlife 强迫你在哪里上厕所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马泰·布莱克洛克(Matai Blacklock)在莱克波特俱乐部的露台上开会。摄影师:安妮·特里特(Annie Tritt)为彭博商业周刊拍摄整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既像工作又像夏令营。与会者并不是选择了彼此,但他们也有点选择了。此外,自然的壮丽景色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夜晚,团队在远离房子的热水浴缸下星空下聚会,周围是沙漠灌木。太黑暗了,看不清面孔,这让交换那些永远不会出现在Instagram上的轶事变得更容易,包括如何回答朋友和初次约会时关于 #vanlife 强迫你在哪里上厕所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生活在他的面包车里的元宇宙营销人员杰夫·贝雷兹尼说,当人们意识到他没有固定住所时,他们会对他有所不同。他说:“如果我说我在面包车里旅行,他们会说,‘我一直想做那个,’那一刻,我就是世界上最酷的人。”其他人在热水浴池的角落里笑了起来。他继续说:“但是如果他们问,‘你是住在面包车里吗?’然后你说,‘是的,’那么就会有人说,‘但是你有家吧?你住在哪里?你无家可归吗?’”
更有经验的游牧民也习惯了被问及关于 《游牧民族》,这部以2020年为背景的电影,由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扮演一位倒霉的女人,当她支付不起其他选择时,开始住在她的房车里。里帕特说她能理解一幕,麦克多蒙德角色无法在朋友家的客房里入睡,半夜退回熟悉的狭小空间的场景。但就像电影中一样,面包车生活可以揭示一些关于阶级和种族的尴尬真相。一些移动车辆的成本为3000美元,而另一些则高达25万美元,许多 #vanlife 的形象是明显的白人。而在路上的生活意味着始终担心安全问题,比如要在车上安装哪些锁以及如何避免警察敲打你的车窗,Kift 的订阅模式承诺提供安心以及素食餐。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许多 Kift 的顾客无法理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将住在车里作为最后的选择。
Amy Zhen,Meta Platforms Inc.的一名设计师,梦想着过上面包车生活四年,直到她和拍档分手并租了一辆Sprinter。当她到达围场时,她立刻感到宾至如归。在第一周,她和新的室友们讨论了生活转变、关系和非一夫一妻制。她说:“这几乎像是一场喜悦的爆炸。”“我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件事的呢?”
这很像奥唐奈想要告诉那些对他的产品不感兴趣的人的故事。他说,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多不快乐。有一次,在回到基夫特家的路上,他和我开车经过了约书亚树郊区一排米黄色、相似的一层楼房。“郊区的梦想,”他干涩地说。“两个人住在一个大盒子里,他们与社区的联系是通过电视和看情景喜剧。”
他的替代方案是否可持续尚不清楚。基夫特已经从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中筹集了数百万美元,但奥唐奈表示未来的资金将直接来自基夫特的客户和粉丝。他计划出售非同质化代币,让买家参与决定基夫特下一个设立地点。他和萨克拉尼说,扩展业务需要一段时间,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重点是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快。除此之外,他们需要为冥想、悠闲晚餐和下一次长途驾驶留出时间。
在柏林西北部的一个新住宅开发项目中,第一批公寓在八月份已经准备好迎接租户,不久之后,一位来自国外的投资者准备收取租金支票。
点击这里 查看德文版本。 订阅 我们的德文通讯。
位于西门子城工业区附近的哈尔斯克索嫩花园项目——一个拥有从单间工作室到家庭式公寓共1,000个单位的项目——在11月被总部位于达拉斯的CBRE集团以3.57亿欧元(3.8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个物业包括另外两个地点,显示了柏林住房市场吸引买家并抵制了更高融资成本的迹象。
 柏林的哈尔斯克索嫩花园项目,于2月13日。摄影师:Krisztian Bocsi/Bloomberg尽管德国各地的房价下跌,但首都的居民持续涌入,而滞后的住房建设导致了供应短缺。这导致了租金可能上涨的前景,深口袋的投资者渴望利用这一机会。
柏林的哈尔斯克索嫩花园项目,于2月13日。摄影师:Krisztian Bocsi/Bloomberg尽管德国各地的房价下跌,但首都的居民持续涌入,而滞后的住房建设导致了供应短缺。这导致了租金可能上涨的前景,深口袋的投资者渴望利用这一机会。
根据在线房地产经纪公司Immowelt的数据,经过利率上调后,柏林的房价连续四个月上涨。在2023年第四季度,柏林是唯一一个房价增长超过1%的大德国城市——相比之下,法兰克福下降了2.6%,慕尼黑下降了0.5%。
“国际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柏林,”领导房地产管理公司JLL柏林住宅投资团队的安德烈亚斯·波尔特表示。除了进一步租金上涨的前景外,他说吸引人的地方是柏林相对来说是一个价格较便宜的欧洲首都,并且拥有庞大的租赁市场——只有15%的柏林人拥有自己的住房。
柏林的复苏与其他因供应不足而受到挤压的主要城市一致。斯德哥尔摩曾是欧洲住房危机的焦点,但根据彭博城市追踪器的数据,瑞典首都连续八个月出现同比增长。
柏林租金上涨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德国城市
年度新建租金同比增长的全国平均值为7.7%
来源:Scout24 WohnBarometer
根据从各种提供商那里汇编的每月数据,彭博监测的十一个市场中有七个市场出现增长。有些是要价和指示水平,而另一些是交易的官方数据。雅典、马德里和里斯本最为强劲,而巴黎和维也纳则在下滑。
点击这里订阅 City Tracker 的故事。
柏林的房价同比下降,并在一月份月度下降,这是一个传统上的淡季。
彭博城市追踪器:城市价格快照
以欧元每平方米计价。变动以当地货币计算
来源:Immowelt(柏林)、Idealista(马德里、里斯本)、Svensk Mäklarstatistik(斯德哥尔摩)、Rightmove(伦敦)、Immobiliare(米兰)、Immopreise(维也纳)、Le Figaro(巴黎)、Properstar(苏黎世区)、Properstar(苏黎世州)、中央统计局CSO(都柏林)、Spitogatos(雅典)、彭博计算。
住房已成为德国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紧张话题,因为缺乏负担得起的住房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的执政联盟未能兑现每年建造40万套住房的承诺,所有三个政党在民意调查中都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
“住房竣工数字令人深感担忧,”德国房地产联合会总经理Aygül Özkan说道。“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75万套公寓的短缺。”
柏林是德国住房困境的中心。20年前,当城市的债务促使社会住房抛售时,柏林被认为是“贫穷但性感”的代表,而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和缓慢的建设早已结束了那个时代。
阅读更多: 柏林贫瘠的住房市场正将其科技繁荣置于风险之中
现在,新来者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找到负担得起的居住空间,IRC Relocation的负责人Niklas Almerood说。“搬到柏林的人比可用公寓还要多。”
 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其复苏与其他因供应不足而受挤压的主要城市一致。摄影师:Krisztian Bocsi/Bloomberg整个城市的政治压力很大,但在像克罗伊茨贝格这样时尚的、曾经是工人阶级社区的地方尤为紧张,许多当地人已经被挤出。2021年,一项要求当局征收大型房东以补充公共住房库存的公投获得通过。这一基层运动部分是对2020年冻结租金努力失败的反应。
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其复苏与其他因供应不足而受挤压的主要城市一致。摄影师:Krisztian Bocsi/Bloomberg整个城市的政治压力很大,但在像克罗伊茨贝格这样时尚的、曾经是工人阶级社区的地方尤为紧张,许多当地人已经被挤出。2021年,一项要求当局征收大型房东以补充公共住房库存的公投获得通过。这一基层运动部分是对2020年冻结租金努力失败的反应。
尽管该立法在法庭上被否决,但它导致了进一步抑制租户供应的后果。随着可供选择的选项减少,人们预计租金将继续上涨,因此更多的租户正寻求摆脱这种上升螺旋,据房地产经纪公司Savills称。
“即使是有偿付能力的家庭也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租房公寓,” Savills德国研究部副总监Matti Schenk说道,他补充说这种转变正在推动柏林房价的逆转。
2022年,随着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逃离俄罗斯的入侵,柏林的人口增加了超过8万人,这还不包括稳定数量的学生和技术工作者。同一年,该市仅建造了略多于1.7万套新公寓。总体而言,过去十年中,住房建设几乎每年都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更高的融资成本也可能为大型投资者提供抓住租赁物业的机会,比如Halske Sonnengärten。这个项目是德国最大房东Vonovia SE的一个单位出售的。许多房地产公司在廉价货币时代负债累累,现在不得不出售物业进行再融资。
 找到负担得起的居住空间是许多新来柏林的人面临的最大障碍。摄影师:Krisztian Bocsi/Bloomberg新建筑远比较老建筑更具吸引力。根据房地产融资平台Europace的调查,德国范围内,老建筑的价格仍在下跌,这些建筑通常有租户签订的较便宜合同,存在大规模翻新成本的风险。与此同时,新项目在同一时期录得了轻微增长,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找到负担得起的居住空间是许多新来柏林的人面临的最大障碍。摄影师:Krisztian Bocsi/Bloomberg新建筑远比较老建筑更具吸引力。根据房地产融资平台Europace的调查,德国范围内,老建筑的价格仍在下跌,这些建筑通常有租户签订的较便宜合同,存在大规模翻新成本的风险。与此同时,新项目在同一时期录得了轻微增长,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陷入困境的Adler Group SA去年底还出售了柏林的一组新设施组合,最近一项法院裁决关于其60亿欧元重组计划可能加速处置计划。
这座城市很可能会继续是投资者的首选,根据JLL的波尔特说。“尽管存在征用的争论和对租赁市场的干预,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柏林仍然是一流的,”他说。
本故事是在彭博自动化的协助下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