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期,被冠状病毒打断 - 彭博社
Sarah Holder
 一份来自年轻成年人在家中生活的疫情剪贴簿。照片拼贴:Sarah Holder在冠状病毒关闭他们的大学、消失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或 derail 他们的职业生涯之前,数百万美国的“新兴成年人”已经被困在家中。2000年至2017年间,25至34岁与父母同住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了22%。
一份来自年轻成年人在家中生活的疫情剪贴簿。照片拼贴:Sarah Holder在冠状病毒关闭他们的大学、消失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或 derail 他们的职业生涯之前,数百万美国的“新兴成年人”已经被困在家中。2000年至2017年间,25至34岁与父母同住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了22%。
归咎于糟糕经济的冲击。2001年和2008年的经济衰退,加上工资差距、不断上涨的大学费用和沉重的学生债务,使得年轻的美国人迟迟未能达到传统的成年里程碑,如结婚、购房和生孩子。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与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相比,千禧一代——“最不幸的一代”——经历了最慢的经济增长。现在从大学毕业的Z世代成员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印度尼西亚庆祝一个正在努力成形的新首都蒙特利尔市中心部分地区因水管破裂而被淹没伊斯坦布尔面临繁忙街道下的危险“火车爱好者”组织支持哈里斯和沃尔兹的总统竞选冠状病毒并没有带来帮助。面对封锁的春天,现在又是一个无目的的夏天,年轻人开始大规模迁回他们曾与父母共享的家。对于最近毕业的年轻人和千禧一代来说,在一个坚固的屋檐下度过经济不确定性是有道理的:他们也是更有可能生活在租金高涨的城市里,而早期的失业统计数据显示,他们在裁员后已经处境更糟。
疫情还引入了其他更情感化的回归原因。被困在与室友的小公寓里,无法控制他们的冒险行为,失去了城市生活所宣传的流动性和乐趣,脱离了实体办公室,并仍在学习基本的成年生存技能,一些年轻人渴望家庭的熟悉感。其他人则被需要照顾或陪伴的焦虑父母吸引回来,或者被疫情带来的奢侈品如汽车、后院和家常饭菜所诱惑。随着死亡人数上升,许多人自己也感到焦虑——担心自己或所爱之人会孤单地遭受疾病。
无论撤退的原因是什么,这场伟大的倒退可能会留下持久的印记,专家们表示。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成年人的感觉:其中一些是独立生活或经济独立,或者有一份事业或组建家庭,”专注于过渡阶段年轻人的心理学家苏珊·安德勒说。新冠病毒使很多事情暂停,可能会让人们面临更长期的惰性。“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一种拉锯,”她说。“有一种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有向后拉的力量,因为成长是可怕的;那是未知的,你不知道另一边是什么样子。”
随着酒吧和俱乐部关闭,社交生活暂停,向后的拉力可能会感觉更强。“当成为成年人的吸引力不再时,”安德勒说,“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但是,冒险、探索和在现实世界中犯错是身份形成的一部分:“在你旧的自我周围,很难想象你想成为谁。”
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许多年轻人没有返回巢穴的奢侈,或者没有房子(或自己的卧室)可以回去。正如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多代同堂的环境中,超过一百万千禧一代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父母;与其变得依赖,许多人反而被迫扩展自己的照顾者角色。即使你不在父母家,新冠病毒时代也不是冒险的时机。
随着几周变成几个月,我与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Z世代和一些真正的千禧一代(最多39岁)交谈,了解他们回到父母身边的感受,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看法。他们回家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许多人都在经历一种既令人恐惧又令人安慰的感觉——打断了他们独立的生活,陷入了不确定的状态。在熟悉的高中海报和旧照片的背景下,他们在悲伤、争吵和梦想未来。我发现,与其说是完全的倒退,不如说在家自我隔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个人成长:在再次奔向成年之前的反思暂停。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按他们的原话整理和编辑以便清晰。
**“**在家待了这么久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安·陈,23岁
**家乡:**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
**疫情前的居住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搬回家:**三月中旬
 安和她的母亲Tee在一个施粥所。图片由安·陈提供我在波士顿和多切斯特长大,这是波士顿大区一个有着相当强大越南社区的地方。我去宾夕法尼亚州上大学,然后在2018年回来了。我选择再次住在波士顿,以重新扎根,并在探索未知之前在家待一段时间。我想感受到来自我妈妈和我非常亲近的祖父的支持,同时也支持他们。我和妈妈一起住了大约六到八个月。
安和她的母亲Tee在一个施粥所。图片由安·陈提供我在波士顿和多切斯特长大,这是波士顿大区一个有着相当强大越南社区的地方。我去宾夕法尼亚州上大学,然后在2018年回来了。我选择再次住在波士顿,以重新扎根,并在探索未知之前在家待一段时间。我想感受到来自我妈妈和我非常亲近的祖父的支持,同时也支持他们。我和妈妈一起住了大约六到八个月。
我们的关系在那段时间真的恶化了。我觉得她很难把我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她]是一个单身妈妈,家庭很小,我们之间有一种强烈而独特的关系: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同时也有一种对父母尊重的期望。长时间不在家,并且对那种家庭结构没有真正的兴趣,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我在九月份做出了搬出去的决定,这对她来说真的很困难。她对此非常不满,这也是我们关系中的另一个争执点。我是独生子女;她有很多期望。我觉得在一个亚洲家庭中,搬出去的想法并不被很好地接受。我想她理想中希望我能永远和她住在一起。
我留在波士顿,离她几英里,和朋友们住在一起,发现自己快乐了很多。我也能更好地管理我们的关系。每周我们都会一起吃早午餐,做一些爱好或家务,建立了一种新的见面节奏,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我觉得距离真的治愈了我们的关系,让我感觉自己在做独立的决定。
然后疫情发生了。我的室友们回家了[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我试着和我妈妈一起待在家里。搬回去在很多方面都很困难,但我觉得从分开生活中学到的教训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可管理。例如,除了跑腿或吃饭外保持距离,理解我能控制的事情,就是我对她所做的事情的反应。如果她生气或不高兴,我真的无能为力,即使我试图平息局势。
我觉得如果我坚持的话,我本可以留在自己的公寓里,但能够在这里生活并感到安全,与某人面对面而不感到害怕,这是一种巨大的奢侈。否则我感觉我就会孤单。我们一直在海滩上散步;我们每周都在一个施粥厨房做志愿者。我们的争吵源于这些无意间的情况,她几乎感到被我不想和她共度时光的想法威胁。因此,我努力确保我们的互动和共度的时光得到很好的对待或欣赏。
我一直在思考作为独生子女的成长经历。前几周,我在拼拼图,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情景,那时我会在浴室里独自坐上几个小时,洗完澡后就这样——我戴眼镜,没有眼镜我几乎看不见,所以我就不会真的盯着任何东西。几乎有一种静谧感,我觉得作为独生子女会带来这种接受静谧的感觉,而我觉得在三月之前我与这种感觉非常遥远。每个周末都有计划。我会和某人一起吃早午餐,然后去办事,接着吃晚餐,晚上去参加某个活动或派对。现在听起来这些事情都如此疲惫。很难想象以那种能量重新融入社会。
在秋天,我将搬到伦敦读研究生。入学前我对新冠的担忧主要是对——只是有点承认我现在工作和家中的奢侈。外面有很多人失业,正在挣扎,而我主动选择放弃这份可以非常舒适的工作和时期,感觉几乎有些荒谬。我觉得我的心态在过去几周发生了变化。几乎就像,因为生活是如此脆弱,我应该这样做,追求我的兴趣,并尝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长。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尽管如此。
“我以前的名字到处都是”
安德鲁*, 30
家乡: 中央弗吉尼亚
疫情前的地点: 华盛顿特区
搬回家: 四月初
*姓名已更改以保护其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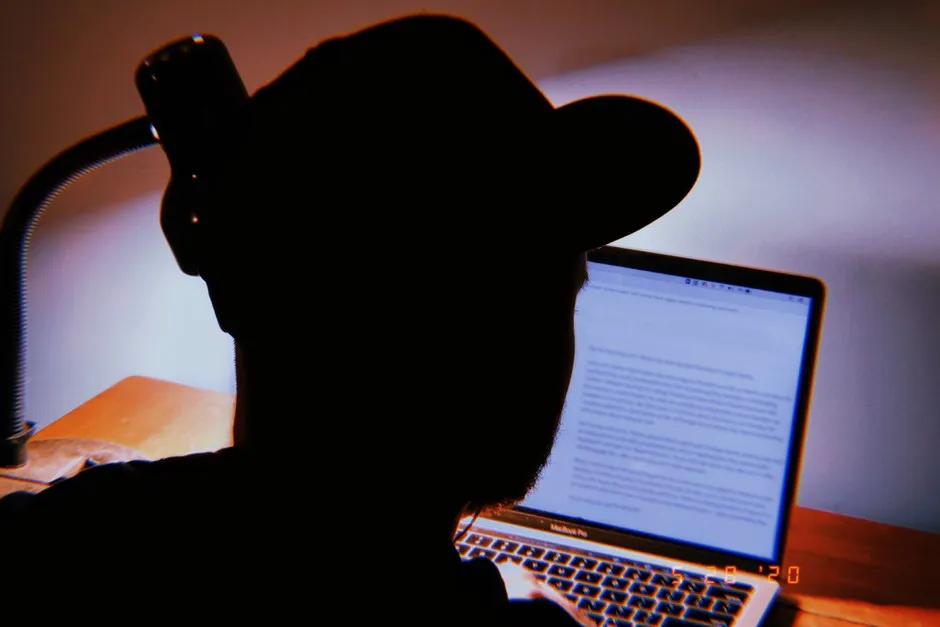 安德鲁,在中央弗吉尼亚的父母地下室。由安德鲁提供我最近和多年的伴侣分手了,所以我不得不找一个新公寓。在这一切开始的时候,三月份,我搬进了一所我和室友没有预先关系的合租房。
安德鲁,在中央弗吉尼亚的父母地下室。由安德鲁提供我最近和多年的伴侣分手了,所以我不得不找一个新公寓。在这一切开始的时候,三月份,我搬进了一所我和室友没有预先关系的合租房。
我在华盛顿特区封锁期间住了大约两个半星期,状态很好。但后来我发现我的室友的女朋友是一名医疗工作者,正在照顾新冠阳性患者。我问过她们是否可以在女朋友过来的时候,只在我室友的房间或外面待着,而不是在公共空间里——我的室友告诉我我太紧张了,我的偏执对她的心理健康不好。
所以经过几夜失眠,我决定最好的选择是搬回父母家,这个决定让我很有压力。我是一个跨性别者,我们一起经历了相当艰难的岁月。我的父母对我转变的态度非常不支持;我爸爸直到我23岁才叫我正确的名字。几乎每次我在大学期间回家,我们都会争吵。这对我心理上来说太过沉重。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住在这里了——大学毕业后的每个夏天,我都待在我的大学城。
我在18岁时向他们出柜——也就是12年前——所以我想,也许现在会好一点:我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安全,并且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持系统。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但在过去几周里,显然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已经无法再一起生活了。
他们并没有毫无理由地粗鲁。他们并不是想要争论。他们并不是想要反跨性别。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好。例如:我在隔离期间给自己剃了个平头,我妈妈对此并不高兴,她一直告诉我需要留长发。这让我感觉与跨性别有关。因为我们成长过程中,妈妈常常告诉我我穿的衣服不合适,而我对自己身体的决定对我来说是肯定的,但在她看来却是错误的。
再说一次,我30岁了,我在12年前出柜。上周我意识到我爸爸在他的手机里仍然没有改我的名字。当然,这是他的权利,但这告诉我他显然还没有放下。
在某种程度上,回到这个物理空间让我感到有些困扰和压力,与我现在的生活有些矛盾。我的旧名字到处都是,还有很多我的旧照片。我被高中时期的这些东西包围着,这让我想起了我感到非常悲伤和被困的时光,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但在其他方面,能够在旧名字周围而不感到压力也让我感到有些赋权;注意到这一点并觉得这很傻,然后继续我的一天。
这也是有趣的——这张桌子是我在2007年意识到自己是跨性别者的地方。我在阅读在线论坛时,恰好读到了一个跨性别男性的经历,然后我意识到,“哦,我的天,那就是我。”所以,带着胡子和我新的男性型秃顶在这里真的很有趣。在高中时,有些时候我觉得生活永远不会朝我想要的方向发展。因为像Covid这样的情况,我在家里真的很奇怪,因为我对此没有控制权——但与此同时,我又身处于我童年的那个物理空间,经历了10年的自主和快乐,意识到我17岁时的状态和我现在30岁的状态之间的对比。真的是太不同了。
如果我长期住在我父母的家乡,我在想,我只会像在华盛顿特区一样通过Zoom与朋友们联系。那么有什么区别呢?但后来我想得更多了。我现在对我居住地的很多思考,实际上是基于我的酷儿社区在哪里。我现在在我的家乡不认识任何跨性别者。作为那些常常被家庭拒绝的酷儿人——无论他们是否有意——那个社区对我来说是家庭的重要替代,我看不出我如何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大量酷儿和跨性别者的地区,他们不仅分享我的身份,还分享更具体的兴趣。我只是不知道我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感觉我生活在我过去生活的壳里”
埃利斯·海曼,23岁
家乡: 加拉巴萨斯,加利福尼亚
疫情前的位置: 皇冠高地,布鲁克林
搬回: 3月17日
 感谢埃利斯·海曼我在2月中旬开始在一家[纽约市]的制作公司工作。到3月初,他们就说,是的,我们要关闭一切。我想,我可能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纽约。我会被困在一个小地方,遇到很多人,而不是被困在一个我不想待的地方,但我有更多的空间,我可以使用汽车,并且可以更好地避免人群。
感谢埃利斯·海曼我在2月中旬开始在一家[纽约市]的制作公司工作。到3月初,他们就说,是的,我们要关闭一切。我想,我可能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纽约。我会被困在一个小地方,遇到很多人,而不是被困在一个我不想待的地方,但我有更多的空间,我可以使用汽车,并且可以更好地避免人群。
我觉得有点懦弱,因为我的朋友们还在纽约,他们在应对,而我回家是为了更舒适。但我很高兴我离开了:我可能会在一个小房间里被困得不太快乐。
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但他们正处于分居的中间。这也是我当初想离开洛杉矶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摆脱所有那些戏剧。现在我又回到了其中。我在不住加州的时候仍然和他们聊得很多,但现在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我爸爸在另一个公寓。
我觉得这对我妈妈真的很好,因为她在过去的10个月里一直很孤单,有人陪伴真的很好,尤其是在现在。你知道,每个人都在网上制作“和伴侣一起隔离与单身隔离”的表情包。我无法想象她有多难。
我的房间自从我高中毕业以来就没有被人动过。字面上说,我墙上的日历显示“2014年6月”,就是我毕业的月份和日期。回到那里就像是完全的时间扭曲。这并不糟糕,但我感觉就像生活在我过去生活的壳里。我想这让我真的在思考我曾经是谁,以及我正在成为谁。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未来,因为我除了坐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这让我非常情绪化和感伤,还有点傻。
短期的未来是尽快回到纽约。但没有人真的知道在这一切平息后会是什么样子——人们说事情会永久改变;我们重构社会和彼此互动的方式。我有点相信,也有点不相信。生活在一个密集的城市地方可能不太有趣,因为事情可能真的会有所不同!
我现在正在领取失业救济,所以我能够支付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这最终会用完。我并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职业可以回去——在娱乐制作行业工作,现在完全暂停了。所以在安全之前,以及我能找到工作之前,真的没有理由回去。未来在目前是非常可塑的,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害怕。
“每一天都悬而未决”
伊莎贝尔,* 22岁
家乡: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疫情前地点: 纽约市
搬回去: 3月12日
*伊莎贝尔要求CityLab不要使用她的姓氏,因为她不想危及她未来的就业机会。
 感谢伊莎贝尔当我最好的朋友第一次建议我们回达拉斯时,我觉得这有点戏剧化。但在我和大学朋友的群聊中,每个人都在问:“谁打算这个周末离开?”我的教师朋友们,他们的学校都关门了。感觉大家都在一瞬间意识到我们需要离开。在三个小时内,我就想,“哇,我需要离开这个城市。”
感谢伊莎贝尔当我最好的朋友第一次建议我们回达拉斯时,我觉得这有点戏剧化。但在我和大学朋友的群聊中,每个人都在问:“谁打算这个周末离开?”我的教师朋友们,他们的学校都关门了。感觉大家都在一瞬间意识到我们需要离开。在三个小时内,我就想,“哇,我需要离开这个城市。”
我一直在想,纽约是一个你想待的城市,因为你总是在外面,你从来不在公寓里——你在拥挤的地方,无论是地铁、餐厅,还是在音乐会上。对我来说,这些就是我想待在纽约的原因。我想,如果所有这些特权——因为它们确实是特权——如果这些都被剥夺了,那么我会很快感到孤独和孤立。我打包准备在家待两周。
我的朋友——那个也从纽约搬回来的朋友——住在离我步行距离内。天气真的很热,所以感觉像夏天。我们一直在说,从我家走到你家,在你的秋千上坐着,感觉像高中。自从大学开始以来,我在外地有暑期工作,所以我真的没有在夏天回过家——尤其是没有事情可做——自高中以来。我周末或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安排。这种感觉创造了一种无忧无虑的感觉——每一天都悬而未决,你知道吗?
我一直想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清理我的桌子、架子或衣柜,然后我意识到我在这里不需要像在纽约那样的最低限度。但当我做那些小清理时,我总是发现旧日记或朋友的旧信件,或者一次性相机的照片。面对生活不同阶段的自己,感觉很奇怪。有时我看到高中毕业时的东西,我想,我觉得那时我是一个更有深思的人,我在想为什么。
 过去的残余。感谢伊莎贝尔在第一个月里,我一直有那种奇怪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被一种特定的记忆击中,让我真的非常尴尬。幸运的是没有什么创伤,但像这样的事情:“哦,我在高中时把一堆番茄酱洒在我朋友的好外套上,那是一个非常尴尬和粗心的时刻。”或者,“哦,我在大学时无缘无故地迟交了那个作业,我觉得现在那位教授——可能不记得我——认为我是个懒惰的人。”
过去的残余。感谢伊莎贝尔在第一个月里,我一直有那种奇怪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被一种特定的记忆击中,让我真的非常尴尬。幸运的是没有什么创伤,但像这样的事情:“哦,我在高中时把一堆番茄酱洒在我朋友的好外套上,那是一个非常尴尬和粗心的时刻。”或者,“哦,我在大学时无缘无故地迟交了那个作业,我觉得现在那位教授——可能不记得我——认为我是个懒惰的人。”
我注意到过去很多时候我没有表现得很有韧性或坚持。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因为我刚毕业一年,还是因为隔离,但我觉得这是我后悔的事情,不断浮现。那些时刻我让某人失望,仅仅是因为我懒惰或没有足够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渴望事情恢复正常,渴望找到下一份工作,以便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是错的。
我也一直在反思,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处于现在的境地,同时也意识到现在发生的事情给美国大多数人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生活——除了让我有更多时间思考我想做什么。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独立住宅的孤立”
艾莉森·瓦滕巴格,28岁
家乡: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地区
疫情前地点: 以色列耶路撒冷
返回时间: 三月中旬
 艾莉森父母的狗在她的童年卧室图片由艾莉森·瓦滕巴格提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在高中之前都是在家上学,我喜欢说这让我为疫情做好了很好的准备。然后我在费城上了高中,之后去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大学,接着在加拿大工作了一年;然后我在杜克大学攻读了三年的神学硕士。之后,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由圣母大学运营的机构做了志愿者。后来这个职位变成了有薪工作,负责与在那里的本科生合作。
艾莉森父母的狗在她的童年卧室图片由艾莉森·瓦滕巴格提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在高中之前都是在家上学,我喜欢说这让我为疫情做好了很好的准备。然后我在费城上了高中,之后去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大学,接着在加拿大工作了一年;然后我在杜克大学攻读了三年的神学硕士。之后,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由圣母大学运营的机构做了志愿者。后来这个职位变成了有薪工作,负责与在那里的本科生合作。
在三月中旬,所有学生都必须飞回家,外籍员工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传言说特拉维夫的机场可能会关闭,我们可能会被困在以色列几个月。我秋天要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我不想被困在以色列。
我一直在反复徘徊,因为我过着这种奇怪的外籍学生生活——去年春天我回到父母那里大约三个月,办理新的签证。这并不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因为某种原因回去这么长时间,但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更愿意留在以色列,那里有一些朋友,但我根本见不到他们,还是回到费城?我没有在那儿生活过,我有高中和大学的朋友和联系,但我没有社区。只有我和我的父母,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我想和他们无期限地生活在一起吗?一切都很顺利——我一直和他们相处得不错。由于过去几年我进进出出,我大概知道回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很有帮助。
我生活中仍然有一些结构——我仍然在做我的一些工作。我的父母都在教书,他们一直教到大学学期结束,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些不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的新例行活动。每天下午4点,我和妈妈一起喝酒和吃奶酪。
但这也很奇怪,走在邻里里,想着,这就是我得知没有进入我想去的大学时的地方。一个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去世了,我参加了社交距离的葬礼。真的很伤心。去参加一个我十年没见过的人的葬礼,大家都戴着口罩和太阳镜,感觉很奇怪。你根本认不出那些你五岁时每天见面的人,他们的脸上全是口罩。这是一种有趣的旧与新混合。
我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棒的小公寓,我住在校园里,我在以色列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在院子对面。每个人晚上都会聚在一起。在那里待了两年让我真的很喜欢住在一个可以和人们一起度过时光的地方,就在隔壁。回到美国,我的父母住在城市边界,但不在市中心,我被半郊区的年轻单身生活所困扰。
再加上美国对疫情的反应,让我想要回到成为外籍人士的生活,并在完成学业后花更多时间在美国之外。现在我们真的感受到单户独立住宅的孤立,我对更社区化的生活方式有一些逆文化冲击的偏好。
“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经常吃家庭晚餐”
米凯拉·哈里斯,24岁
家乡: 马里兰州波托马克
疫情前地点: 华盛顿特区
搬回: 三月中旬
 米凯拉·哈里斯提供我和我的室友一直计划在三月底结束我们的租约,主要是因为我打算在法学院之前请假旅行。(显然这没发生。)她打算搬到纽约(这也没发生)。她的父母都是圣路易斯的医生,所以当疫情在三月开始加剧时,他们说,你必须离开那里。她慌忙打包,两天后我也在慌忙打包。
米凯拉·哈里斯提供我和我的室友一直计划在三月底结束我们的租约,主要是因为我打算在法学院之前请假旅行。(显然这没发生。)她打算搬到纽约(这也没发生)。她的父母都是圣路易斯的医生,所以当疫情在三月开始加剧时,他们说,你必须离开那里。她慌忙打包,两天后我也在慌忙打包。
我的哥哥,21岁,在上大学,春假期间他本来就要回家。他的状态明显比我更退步了。妈妈每天早上叫醒他,并为他做早餐。但他已经21岁了,所以我想这 稍微 有些不同。
我们在每晚家庭晚餐方面保持了一致,但到了现在,由于我们整天都在家,已经没有什么新信息可以分享。有些晚上我们相对安静,其他晚上我们会回忆往事,有时我们会谈论政治。但在高中时,我们的日程安排都非常不同。尤其是因为我父母都在工作,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经常吃家庭晚餐。这有点特别。
当我在这个春天决定法学院时,Covid确实成为了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在我心里,我想,好的,如果我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上学,回家的难度就更大。而如果我在一个开车能到的地方,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知道它就在附近真是太好了。
“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玛丽亚·布茨科夫斯基,26岁
家乡: 密歇根州底特律
疫情前地点: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回迁时间:**三月中旬
 “我爸爸在这次危机中真的很无聊……他买了一个便宜的3D打印机,做了一个旋转滑板车。”感谢玛丽亚·布兹科夫斯基我大约在一年前的七月从华盛顿特区搬到旧金山,当时我一个人住在公寓里。我在旧金山没有车——我每天步行上班,或者可以使用滑板车。我妈妈一直说,这里会容易得多。她非常坚持让我回家,所以我回来了。
“我爸爸在这次危机中真的很无聊……他买了一个便宜的3D打印机,做了一个旋转滑板车。”感谢玛丽亚·布兹科夫斯基我大约在一年前的七月从华盛顿特区搬到旧金山,当时我一个人住在公寓里。我在旧金山没有车——我每天步行上班,或者可以使用滑板车。我妈妈一直说,这里会容易得多。她非常坚持让我回家,所以我回来了。
起初我不想回家,因为我担心如果我没有症状,可能会把我的父母感染;或者在坐飞机后我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我的姐姐住在底特律,所以我在她那里待了14天并进行了隔离。
我在汽车行业的家庭中长大——我爸爸在福特工作了超过40年。我也在Spin工作,Spin是福特拥有的,所以我们不停地谈论我们的工作,这可能让我的妈妈非常烦恼。有趣的是,自从我18岁以来我就没有拥有过汽车。尽管我在一个以汽车为中心的世界中长大,但我从来没有真正依赖过汽车。这场疫情确实改变了人们对交通的思考。
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可以在家工作。我认为这确实让很多人重新考虑——我的意思是,我正在为一个我目前没有居住的地方支付X金额的租金。我的租约在七月结束,我在考虑之后按月租住。我对回到旧金山有点害怕。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我没有预料到压倒性的孤独感”
艾米莉·麦克弗森,22岁
家乡: 德克萨斯州登顿
**疫情前的地点:**俄克拉荷马城,俄克拉荷马州,她在州众议院担任研究员。
**搬回:**四月中旬
 艾米莉和她的狗在她的童年卧室。图片由艾米莉·麦克弗森提供他们在三月中旬让我们回家工作——我们都在上班,然后突然间大楼里有人检测出Covid阳性。起初我并不介意:我比较内向,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真的很珍视我的独立。
艾米莉和她的狗在她的童年卧室。图片由艾米莉·麦克弗森提供他们在三月中旬让我们回家工作——我们都在上班,然后突然间大楼里有人检测出Covid阳性。起初我并不介意:我比较内向,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真的很珍视我的独立。
我妈妈已经发短信给我说:“如果你想开车过来和我们在一起可以,”但那时我想一个人待着。一到四月中旬,我就想,好吧,我需要不再一个人了。
这有点奇怪,因为我刚刚大学毕业,所以在过去的四年半里我一直住在外面,但仍然在经济上依赖我的父母。现在我 刚刚 经济独立了,我自己生活,自己支付账单。尽管这是我的选择,但和他们在一起仍然很奇怪。
我父母的房子很小——几乎可以听到一切。我爸爸在一个房间里开Zoom会议,我妈妈在另一个房间里开Zoom会议,而我幸运的是不需要参加Zoom会议。但我必须观看很多正在直播的会议。我们都在不同的房间,但仍然能听到彼此。当我打电话给朋友或看电视时,我非常清楚他们能听到我——我不会像平时那样和朋友聊天;我不想说脏话,因为我妈妈是幼儿园老师,她会杀了我。
在五月的第一天,我的州重新开放,起初看起来我也得回去。所以在一个最近的星期六早上,我回去了,完全期待着必须待在那里——实际上我一回到家,我的老板就发了邮件说,是的,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继续远程工作。我在公寓里住了一晚,然后第二天开车回去了。
我没想到回到公寓时会有如此强烈的孤独感。起初我在想,“我在父母家过得很好,但很快我就会厌倦它,想要回去,”但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并没有厌倦它!
待在我父母家确实让我明白,当我的公寓租约到期时,我很想租一栋房子。我还远未到可以 买 房子的阶段,但看到我的狗在后院里是多么快乐,以及我在有后院的情况下是多么快乐——我一直在挂我的吊床,有时我在外面工作——我有点内疚把我的狗带回我的公寓。
“我和我妈妈都一直说是时候让我走了”
亚历山德拉·希尼克,39岁
**家乡:**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
**疫情前地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搬回:**3月17日
 亚历山德拉在客厅里做倒立。朱迪·希尼克我在芝加哥上大学,然后在波兰读研究生,曾在法国学习,生活在华盛顿特区、柬埔寨、老挝和黎巴嫩。2012年,我决定搬回美国,觉得纽约似乎是个合适的地方。
亚历山德拉在客厅里做倒立。朱迪·希尼克我在芝加哥上大学,然后在波兰读研究生,曾在法国学习,生活在华盛顿特区、柬埔寨、老挝和黎巴嫩。2012年,我决定搬回美国,觉得纽约似乎是个合适的地方。
今年12月,我辞去了我的工作。我已经计划了大约10年要和我的父母一起回柬埔寨;我攒了假期,申请了三周的假期,但被拒绝了。我说我必须现在去,要不就永远不去,所以我辞职了,什么都没有安排好。
我和我的父母达成一致,如果我很快找不到新工作,我就会回家——尽管这听起来很疯狂,我从来不想这样做。但在我最后一天,当我把东西交给人力资源部时,我收到了来自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另一份工作邀请。这真是太有趣了,因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正考虑回家的选项。
所以我在一月搬到了匹兹堡。然后在3月16日,我爸爸发生了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我在17日来到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陪伴我的妈妈。来这里真的很可怕——我在想,天哪,我会带来冠状病毒吗?但这是正确的决定,待在这里真的很美好。我的妈妈通过Zoom参与了我在匹兹堡的生活——她见到了我的同事和我的瑜伽老师。
我以为这会持续两周,但后来没有理由再回去。我一直在推迟离开;每周我都在想,哦,我再待一周,我再待一周。你失去了对时间的所有感知。当你失去一个父母时,谁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家人一起度过不确定的时间?这太神奇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但我和我妈妈都一直在说,是时候让我走了。我需要离开,去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就像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中——老实说,我仍然觉得我爸爸会回家。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的生日是4月4日,我们举行了一个Zoom生命庆祝会,因为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想要一个大派对。我一直在拖延,但他的兄弟说我们必须做 一些事情。这真的帮助了很多。你知道,就像,“哦,天哪,又一个Zoom”,但这真的很棒。我们将在明年4月举行一个大派对。
关于搬出去的截止日期,我终于决定了。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把父亲节当作一个特别的日子。但这是6月中旬,一个自然的截止点。这给了我时间,也给了我一个整理我父亲所有东西的截止日期。我想这会帮助我处理我父亲实际上已经去世的事实,以及我必须在匹兹堡开始我的生活并继续前进。我期待着帮助建立我生活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