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郊区的另类历史 - 彭博社
Amanda Kolson Hurley
 史蒂夫·布朗斯坦/盖蒂以下是新书的摘录《激进的郊区》(贝尔特出版,$16.95)。
史蒂夫·布朗斯坦/盖蒂以下是新书的摘录《激进的郊区》(贝尔特出版,$16.95)。
在1960年代初,马尔维娜·雷诺兹写了一首名为“小盒子,”灵感来自于在湾区一个新的郊区住宅区开车经过一排排相似的淡色房屋。(她的朋友皮特·西格在1963年用这首歌取得了成功。)雷诺兹将这些千篇一律的房子视为居住在其中的人的从众心态的象征和塑造者——那些只渴望打高尔夫球和抚养将来会住进“千篇一律”盒子的孩子的医生和律师。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芝加哥以冷静、派对和阳光克服DNC怀疑者纳粹掩体的绿意改造将丑陋的过去变成城市的眼球吸引者圣保罗的公寓如何帮助庇护南美洲最大的城市仅使用公共交通的跨洲竞赛但雷诺兹错了,关于住在这个郊区的人的身份,达利市,位于旧金山以南。这里最初并不是她想象中的喝马提尼的医生和律师的家,而是那些在战后住房繁荣中最后一批进入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白人)奋斗者。
然后,仅仅在雷诺兹写下这首歌几年后,菲律宾人和其他来自亚洲的移民开始抵达达利市。雷诺兹所鄙视的“嘈杂”建筑对他们改造和扩建大家庭的房屋来说是可行的,达利市成为了美国的“菲律宾人首都”,在美国拥有最高浓度的菲律宾移民。
陈词滥调和误解仍然在大众想象中定义了郊区,这让我感到疯狂。我住在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位于华盛顿特区之外。我是一个郊区居民,但我的生活并不围绕修剪整齐的草坪、地位焦虑或对同质性的渴望。我的郊区经历是乘坐公交车,周围的人用西班牙语和法语克里奥尔语聊天。我的邻居来自西藏、巴西和肯尼亚,还有辛辛那提。我的儿子在一所反映美国今天多样性和顽固不平等的学校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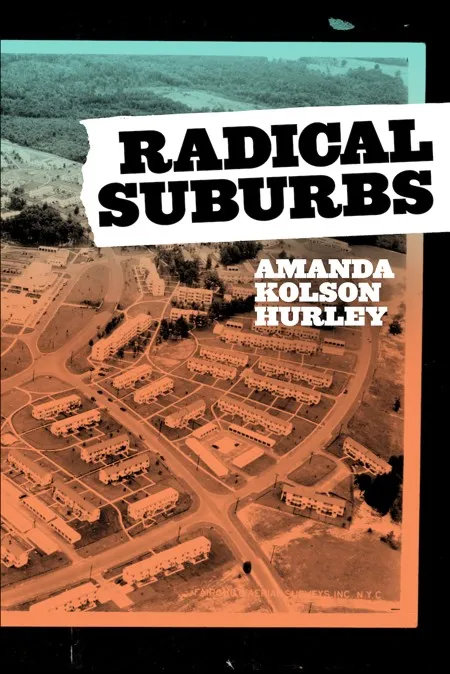 贝尔特出版大多数美国人所知道的郊区基本故事大致如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富人的乡村度假胜地和“电车郊区”在城市的边缘出现。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道路和廉价的政府抵押贷款吸引了数百万白人从城市的公寓和排屋迁移到新开辟的郊区小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逃避非裔美国人最近迁入的社区和学校,这种破坏性现象被称为白人逃离。
贝尔特出版大多数美国人所知道的郊区基本故事大致如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富人的乡村度假胜地和“电车郊区”在城市的边缘出现。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道路和廉价的政府抵押贷款吸引了数百万白人从城市的公寓和排屋迁移到新开辟的郊区小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逃避非裔美国人最近迁入的社区和学校,这种破坏性现象被称为白人逃离。
郊区是这些白人中产阶级美国人可以将自己与感知的城市弊病隔离的地方,在一个静态和受管控的环境中,私人空间、财产拥有、种族同质性和核心家庭是主导价值观。
这并非不真实——但远非完整。激进的郊区是关于一波波理想主义者,他们在1820年代开始在美国东部城市外建立替代郊区,并持续到1960年代。这些群体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和动机,但他们都相信地方社区在塑造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力量,以及郊区土地提供的自由,以新的方式生活和建设。
与那些深入美国内陆定居孤立公社的群体相比,这些人可以用一个听起来矛盾的短语来形容,称为实用的乌托邦者。靠近城市让他们能够在有经济支持和紧急出口的情况下尝试新的生活方式。现在,在一个可以合理地说——国家的未来悬挂在郊区在接下来的20或30年内的作为上,他们的历史表明,勇敢的社会和建筑实验并不是郊区所陌生的。事实上,这是一种郊区传统。
郊区并不是美国或甚至西方的发明。郊区的存在与城市一样久远。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乌尔的郊区延伸到城市之外数英里。在古罗马,城市的边缘是贵族们保持“乡村”度假的地方。但这个区域也是罗马人推开他们不想看到、听到或闻到的地方——例如,像制革和制砖这样的有害工业。
即使在中世纪,城墙也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坚固的界限。郊区区域超出了它们的范围,人和货物往返流动。“在欧洲及其他地方,‘有墙的中世纪城市’多次扩大其围墙区域,以容纳其边缘地带并为未来扩展做准备,”城市学者施洛莫·安吉尔写道。妓女、吉普赛人和麻风病人常常被迫生活在 城外,字面意思是“在城市之下”。这个术语本身就暗示了保护墙的高度以及那些在其怀抱之外的不确定地位。
美国的郊区早于欧洲殖民化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在圣路易斯附近,考古学家最近发现了一个900年前的卡霍基亚郊区的遗迹,曾是墨西哥以北最大的美洲原住民城市。(这个古老郊区的遗址位于现代的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镇,“在一个破旧的肉类加工厂和一个现在关闭的脱衣舞俱乐部之间的半路上,” 正如NPR报道的。)
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有了郊区。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并且仍然如此),这些郊区主要是为低社会经济群体而设。精英们则留在市中心。但19世纪中叶,第一批我们容易识别的郊区开始出现——包括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 伊利诺伊州的河滨和新泽西州的卢埃林公园。这一时期也恰逢家庭崇拜的兴起,提倡家庭主妇作为 “家中的天使,”以及位于远离城市污垢和罪恶的安全距离的独立郊区别墅,作为理想的美国家庭住所。
 一幅理想化的中上层家庭生活的库里尔与艾夫斯石版画。国会图书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围绕美国城市繁荣发展的富裕郊区,英美家庭生活在优雅的维多利亚女王风格和都铎复兴风格的房屋中,如堪萨斯城的 乡村俱乐部区、费城的栗子山和加利福尼亚的比佛利山庄。工业和大多数商业活动常常被驱逐出这些郊区,黑人和犹太人被限制性契约禁止购买房屋。
一幅理想化的中上层家庭生活的库里尔与艾夫斯石版画。国会图书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围绕美国城市繁荣发展的富裕郊区,英美家庭生活在优雅的维多利亚女王风格和都铎复兴风格的房屋中,如堪萨斯城的 乡村俱乐部区、费城的栗子山和加利福尼亚的比佛利山庄。工业和大多数商业活动常常被驱逐出这些郊区,黑人和犹太人被限制性契约禁止购买房屋。
然而,即使在它们的全盛时期,精英聚居区也不是城市边缘的常态。农业在这里仍然蓬勃发展,通常由外籍和非白人农民进行,同时工厂也在侵占。贫民窟点缀着城市的边缘,还有一些简陋的开发项目,人们在荒地上建房,挖井,养鸡和牛,种植蔬菜。在他的书中 他们自己的地方,历史学家安德鲁·维斯讲述了查格林瀑布公园的历史,这是克利夫兰一个自建的黑人郊区,发展到拥有数百名居民、四座教堂、一所小学和一个社区中心。
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公社、殖民地和其他有意的定居点也不断出现在城市附近。 在 许多 例子中,一个名为哈莫尼斯的独身德语宗教团体在1820年代建立了一个美丽而繁荣的小镇,名为经济镇,位于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阿姆布里奇。靠近匹兹堡市场对他们的制造业和旅游贸易(该镇有一家酒店,甚至还有一个博物馆,这是美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至关重要。
和谐派没有私人财产,所有物品共同拥有,镇上的建筑反映了这一点,基础设施如共享的面包烤炉和为节日盛宴准备的社区厨房。不相关的成年人有时一起生活,这与现代的群体住宅并无不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和谐派的社会制度赞不绝口——只是没有宗教。这个教派逐渐人数减少,最终在1905年解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和谐派的社会制度赞不绝口——只是没有宗教。十年后,即1915年,一群松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纽约登上火车,抵达新泽西州中部,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和进步学校——并避开了城市里的警察审查。当他们从水塔上升起红旗时,当地人爬上去将其扯下。但他们或多或少被放任自流,斯特尔顿殖民地在大萧条和许多政治斗争中持续到1950年代。
一些居民通勤到纽约,乘坐早上5:45的火车去服装区工作或出售他们养的鸡蛋。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基本的两到三间房的小屋里。他们在流行之前就已经是微型房屋的居民——并不是因为对极简主义的渴望,而是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出租任何空余房间给房客是补充收入的常见方式。随着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衰退,一些殖民者逐渐离开,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入伍时附近一个大型军营的开放加速了斯特尔顿的灭亡。
 一个孩子在新泽西的斯特尔顿殖民地的小屋前拉小提琴。一些中产阶级的访客对粗糙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感到震惊,但居民们,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尽管资金有限,仍然能够在这里购买土地并建造房屋。特别收藏与大学档案,拉德格大学图书馆战后,私人房屋建筑商——凭借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在数千平方英里的郊区铺开了他们的“盒子”。但对新的住宅区来说,存在替代方案和挑战。
一个孩子在新泽西的斯特尔顿殖民地的小屋前拉小提琴。一些中产阶级的访客对粗糙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感到震惊,但居民们,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尽管资金有限,仍然能够在这里购买土地并建造房屋。特别收藏与大学档案,拉德格大学图书馆战后,私人房屋建筑商——凭借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在数千平方英里的郊区铺开了他们的“盒子”。但对新的住宅区来说,存在替代方案和挑战。
例如,一位名叫 莫里斯·米尔格拉姆 的不寻常的房屋建筑商几乎在其后院挑战了莱维顿的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名前社会主义活动家,米尔格拉姆于1954年开设了一个名为康科德公园的综合性住宅区,包含140栋房屋。它位于费城东北部,距离宾夕法尼亚州的莱维顿几英里。购房者包括几对跨种族夫妇、一些共产主义者和许多不墨守成规的人。他们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而他们的父母则组成了一个保姆合作社,以及保龄球、摄影和缝纫俱乐部——就像其他新郊区的居民一样。
“郊区打破种族壁垒,” 纽约时报 的标题宣布。“费城的新私人住房项目整合了黑人和白人——没有发生任何事件——没有一个家庭从理想和韧性建立的殖民地搬走。”
 1957年在康科德公园举行的每月邻里会议,如《黑檀》杂志所描绘。莫里斯·米尔格拉姆档案 [Coll. 2176],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康科德公园离莱维镇足够近,以至于在1957年,当莱维镇的第一位黑人居民黛西和威廉·迈尔斯遭到愤怒人群骚扰时,邻里派出一个跨种族小组前去守护他们的家。
1957年在康科德公园举行的每月邻里会议,如《黑檀》杂志所描绘。莫里斯·米尔格拉姆档案 [Coll. 2176],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康科德公园离莱维镇足够近,以至于在1957年,当莱维镇的第一位黑人居民黛西和威廉·迈尔斯遭到愤怒人群骚扰时,邻里派出一个跨种族小组前去守护他们的家。
即使在其反文化的变体中,战后郊区的规划仍围绕着全职妈妈、爸爸和小杰克与小莎莉展开。如今,美国的单身人士、单亲家庭和多代同堂的家族数量超过了有幼儿的核心家庭。千禧一代由于工资微薄和大量学生贷款债务,往往无法负担他们成长时的郊区分层住宅。而且即使他们能买得起,很多人也不想买。
这成为无数趋势文章的素材,但千禧一代确实有对城市生活的偏好。民意调查 显示他们重视能够步行到商店和餐馆以及短途通勤。年轻成年人还报告称,他们在城市中比前几代人在同一生活阶段时更快乐。
我们可能正处于“伟大的反转”,正如作家艾伦·埃伦哈特所称:全国从战后富裕郊区和贫穷城市的模式,回归到精英城市和低端郊区的历史常态。即使我们不是,然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人口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化——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郊区是为谁和什么而存在。
目前,一些郊区正在适应新的现实,转变为拥有步行市中心、轻轨线路和更密集住房形式的“城市郊区”。这种有意识的城市化在满足年轻人偏好方面是聪明的。但这也是唯一负责任的做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在2018年10月的报告中警告说,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窗口——直到2030年——来降低排放,以避免灾难性的变暖,而做到这一点将需要“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快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化”。
研究表明,蔓延式土地使用通过去中心化工作和服务并促使我们更多开车,从而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到处开车的人也更少活动,因此更容易患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郊区,像城市一样,需要更多的社区,让居民可以步行满足日常需求;优先考虑行人、自行车和轻轨及公交车的街道;以及高质量的公共空间。改造郊区,引用艾伦·邓汉-琼斯和琼·威廉姆森的话,她们写了一本同名书籍,是“本世纪的大项目”。
 不幸的是,郊区在那些能够改善它们的人中间存在一种污名:建筑师。设计精英们多年来交替地对郊区表示赞助或抨击,自从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称郊区为“在城市墙壁上翻滚的一种污垢”以来。
不幸的是,郊区在那些能够改善它们的人中间存在一种污名:建筑师。设计精英们多年来交替地对郊区表示赞助或抨击,自从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称郊区为“在城市墙壁上翻滚的一种污垢”以来。
比利时建筑师莱昂·克里尔声称:“郊区恨自己”,他以对传统城市主义的赞美而闻名于世,发表了许多争议性的著作和漫画。对克里尔来说,郊区本质上是寄生虫,是一种恶性肿瘤。“它知道自己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想要征服世界,因为它无法与自己和解,”他写道。“郊区通过包围城市来扼杀城市,撕裂城市的心脏。郊区只能生存,不能生活。”
早期实验性郊区的居民认为他们生活在僵尸社区的想法是可笑的,他们相信自己是开拓者,并热情地投入公共生活。在马里兰州的格林贝尔特,一个由联邦政府作为新政的一部分建立的进步示范城镇,一些居民认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沿着不同、更合作的路线重绘社会的模式。一位格林贝尔特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给华盛顿一家报纸写信时说:
我们在格林贝尔特学会了,尽管作为个体我们是微弱的,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有力量。我们学会了团结社会行动的重要性和潜力——如果我们的民主要生存,我们的人民还必须学习什么更伟大的教训呢?
乔恩·索托·斯科特,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曾在斯特尔顿殖民地长大,他告诉我:“我认为这是任何人都能拥有的最好的童年。”劳拉·托马斯,一位退休的数学老师,记得在1960年代以极大的怀疑态度去看弗吉尼亚州的综合新城雷斯顿。她是非裔美国人;她为什么要搬到弗吉尼亚呢?但她最终在那里定居,组建家庭,并参与了公民团体雷斯顿黑人焦点。
早期居民对这些实验性郊区生活在“僵尸社区”中的想法会感到可笑。“无论[雷斯顿的创始人罗伯特]西蒙做了什么,无论信息是什么,无论他如何宣传——我无法确切说出,”托马斯说。“他吸引了在种族和社会经济上非常不同的人。但他们在对待人的观点上有共同点。这成为了雷斯顿的普遍特征。”
克里尔的话背后是对郊区混合特质的厌恶——它如何混淆城镇与乡村、人造与自然的明确二元对立。我听到过同样的情绪,抱怨郊区是“两种世界的最糟糕之处”——比乡村更拥挤和繁忙,却比城市更无趣。
但如果我们选择拥抱郊区的中间状态,而不是谴责它呢?在过去的150年里,郊区居民生活在大型公寓和小棚屋、现代公寓和新哥特式豪宅中。他们是租户和房主、家庭佣人和企业高管。他们既培育翡翠般的草坪,也种植农作物。他们寻求逃避社会进步,追求摆脱常规的自由。
严厉的分区和土地使用法规可能试图让时间静止,但郊区的未来并没有什么是注定的,而大多数美国人都生活在这里。与其对郊区的问题感到绝望,我们应该受到郊区历史的启发,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正如斯特尔顿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知,以及在莱维顿的迈尔斯家旁守夜的康科德公园居民所知:郊区是我们所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