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城市》谈规划如何跟随房地产 - 彭博社
bloomberg
 位于纽约市中央公园南侧的新超高塔楼中央公园塔、111 W 57街和53W53正在建设中。卢卡斯·杰克逊/路透社全球房地产的估计价值为217万亿美元,占全球资产的60%以上。尽管其中四分之三的金额与住房相关,但这并没有为许多人带来安全的住所或繁荣:2016年,美国的住房拥有率达到了50年来的最低点,而在同一年,美国所有房屋销售中有37%是卖给了缺席投资者。
位于纽约市中央公园南侧的新超高塔楼中央公园塔、111 W 57街和53W53正在建设中。卢卡斯·杰克逊/路透社全球房地产的估计价值为217万亿美元,占全球资产的60%以上。尽管其中四分之三的金额与住房相关,但这并没有为许多人带来安全的住所或繁荣:2016年,美国的住房拥有率达到了50年来的最低点,而在同一年,美国所有房屋销售中有37%是卖给了缺席投资者。
随着华尔街支持的邀请之家(由黑石集团拥有)现在成为全国最大的单户住宅房东——收购了许多十年前被止赎的同类物业——很难将住房拥有的承诺视为美国梦的一个原则。并不是说租房就容易得多:过去二十年,美国的平均入住租金已经翻了一番以上。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芝加哥以冷静、派对和阳光克服了DNC怀疑者纳粹掩体的绿意改造将丑陋的过去变成城市的眼球吸引者圣保罗的Cortiços如何帮助庇护南美最大的城市跨洲际公共交通竞赛这些挑战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以做些什么?尽管许多城市规划者希望解决住房危机,但获得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公共补贴的重建项目迫使他们做出妥协,塞缪尔·斯坦在他的新书中辩称资本城市:绅士化与房地产国家(Verso,$1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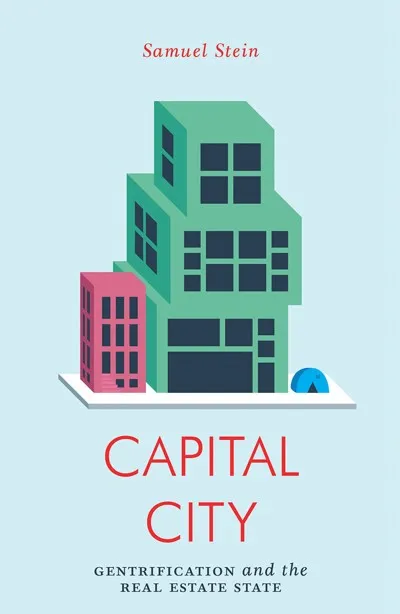 Verso斯坦认为,开发、金融和全球精英将财富停放在豪华住房中的综合力量淹没了规划者的最佳意图。随着大多数工业活动被推向城市边界之外,公共服务依赖于财产税,他认为,房地产已经主导了城市规划;科技和金融部门对此依赖,并未提供任何政治制衡。
Verso斯坦认为,开发、金融和全球精英将财富停放在豪华住房中的综合力量淹没了规划者的最佳意图。随着大多数工业活动被推向城市边界之外,公共服务依赖于财产税,他认为,房地产已经主导了城市规划;科技和金融部门对此依赖,并未提供任何政治制衡。
斯坦写道,国家是“绅士化的中心参与者”。规划者一方面通过土地使用和税收激励吸引开发商和房东,同时另一方面通过便利设施吸引新居民和购物者——所有这些都推高了价格。“规划者的使命是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他们的日常工作涉及创造一个更有利可图的世界,”他写道。本书的一章追踪了特朗普家族三代人的房地产交易,这些交易在不同时间受到公共政策和个人利益激励的推动。
对于斯坦——一位在纽约市立大学攻读地理博士学位的候选人、亨特学院的讲师以及受过培训的规划师——规划问题是理解我们当前经济秩序的核心,尤其是在城市生活中的体现。CityLab询问了他关于房地产的崛起、激进的规划师以及有志成为规划师的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角色的问题。(本次采访经过编辑和压缩以便于理解。)
您认为房地产的崛起和工业主义的衰退(工业主义需要低土地成本和可负担的住房以供工人居住)正在如何改变规划师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规划师的响应能力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房地产日益集中的资金中,规划师对普通民众的响应能力正在减弱,他们没有一群独立的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在一旁对他们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
我认为我们常常希望能够告诉规划师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然后让他们去做其他事情,但这并不是系统的运作方式。规划师主要是遵循委员会和市长任命的规划部门负责人的指令,而在大多数大城市中,市长们从房地产中获得了大量资金,即使是那些承担反对城市更新责任的人,比如纽约市。规划师很难简单地看到某些事情是错误的并加以修正。我不想让他们逃避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但我也不希望人们期待他们仅仅因为应该改变就去改变。在目前的结构下,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你为什么强调在日益不平等的城市地区规划的重要性?
在美国的背景下,规划者被低估——不仅作为个体,规划的行为也被轻视。我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弄清楚他们的城市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的住房成本如此疯狂,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规划者,而是将他们作为一种切入点,理解资本、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房地产中金钱的日益集中,规划者对普通人变得越来越不敏感。”我受过规划方面的训练,所以我理解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做什么,我确实相信他们是一群非常友好的人。我把手稿发给了一位建筑师朋友,这个说法引起了她的共鸣:她说,‘这真的很真实[规划者是好人],而且没有人会这样说建筑师。’所以有趣的是,这群善意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负面转变。
你有一章专门讲述特朗普家族的房地产事业——不仅是总统,还有他的父亲和祖父。你认为他们的故事如何帮助解释当前房地产和政治的动态?
现在他是总统了,我们往往会沉迷于所有的丑闻和日常的愤怒。但我想提醒人们,不仅仅是抽象的房地产资本在获得权力。这在我们政治层级的第一位置上得到了体现。
[特朗普]家族让我们看到城市规划历史的另一面——这不仅仅是规划者及其对城市的影响,还涉及到是谁在推动他们做这些事情。特朗普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但关键并不是他们是例外;而是他们在利用公共政策和补贴谋取个人利益方面是普通的[因为他们从未处于纽约房地产的巅峰]。真正例外的是他们中的一个现在是总统。
你讨论了一种激进规划的遗产,这教会了积极的规划者“虽然他们可能在工作场所是孤独的,但他们在工作队伍中并不孤单。”
长期以来,叛逆的规划者历史悠久,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模式。曾经有过平等机会规划者(PEO),试图将城市规划者与反城市更新运动联系起来。还有规划者地下组织,这是一个更激进的规划者运动,他们向活动家泄露城市正在做的事情的信息,并撰写匿名证词和给编辑的信件。
哈莱姆建筑师复兴委员会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规划者积极提升哈莱姆工人阶级想象自我决定在空间上会是什么样子的能力。然后你会看到 规划者网络,它源于[PEO],作为一个左翼城市规划者的组织,可以与美国规划协会对立。这个组织仍然存在,我认为它是希望超越新自由主义及其特定工作的规划者的重要资源。
我认为这种激进的城市规划者仍然有其角色,不仅在系统外,也在系统内。人们必须组织起来,而不仅仅是在个人的自由时间里做,而是要集体行动,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对规划者施加的群体思维。当你在系统内部工作时,往往会被告知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这些事情只是对掌权者来说不受欢迎。我认为,思维不同的规划者在工作之外聚在一起,思考和制定策略,寻找他们如何能成为挑战其上司的运动的资源,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会对那些对城市规划领域感兴趣的人说些什么,作为他们考虑这项工作的建议?
我会鼓励他们始终保持批判性思维,不要气馁。我认为规划中有一种强烈的务实倾向,这在将激进思想转化为可行方案时是有价值的。但这也可能抑制激进主义和远见思维,甚至是乌托邦主义,而这在知道我们希望在哪里时也是有用的。
我鼓励人们坚持这些冲动,找到与他们有相同想法的人,或者挑战他们自己思维的人。在孤立中,系统吞噬我们,但集体行动可以让我们想象出更好的城市规划方式,并与那些挑战他们的社会运动相连接。关键在于不去强加那些作为专业规划者施加给我们的限制,而是成为这些运动的资源,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更正: 本文的原始版本错误地识别了塞缪尔·斯坦的博士候选人身份;他是在纽约市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