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胺酮可能很快用于治疗自杀意念 - 彭博社
Cynthia Koons, Robert Langreth
 乔·赖特在2018年12月15日的纽约市。
乔·赖特在2018年12月15日的纽约市。
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为《彭博商业周刊》拍摄乔·赖特毫不怀疑氯胺酮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位34岁的高中教师每天在打字机上写诗,多年来一直受到自杀冲动的困扰。这些想法在他自己还是高中生时就开始出现,地点在纽约斯塔滕岛,并在大学的第一年加剧。“这是一种内心独白,强调存在是多么无意义,”他说。“就像被自己的大脑伏击。”
他第一次试图通过吞下整瓶安眠药在大二的夏天自杀。随后经历了多年的治疗,包括普乐安、佐洛福、威尔布林和其他抗抑郁药,但对结束生命的渴望从未完全解决。他开始用铅笔刀片在手臂和腿上自残。有时他会用香烟烧自己。他对第二次和第三次自杀尝试的细节记得不多。那些尝试都是心不在焉的;他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还混入了安定。
赖特决定在2016年再试一次,这次使用他研磨成粉末的药物鸡尾酒。现在回忆起这个故事时,他正在准备将粉末混入水中饮用,这时他的狗跳到了他的腿上。突然间,他有了一个震惊他的清晰时刻,促使他采取行动。他开始做研究,发现了一项关于严重抑郁和自杀倾向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该研究涉及氯胺酮的输注,这是一种已有几十年历史的麻醉剂,同时也是一种 臭名昭著的派对药物。他立即自愿参加。
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氟烷麻醉注射让他感到梦幻、傻乎乎的和欣快的。他几乎立刻开始对生活感到更加希望。他对治疗的接受度更高。不到一年后,他结婚了。今天他说他的抑郁情绪已经遥远且可控。自杀念头基本消失了。“如果他们告诉我这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是不会相信的,”赖特说。“不让它已经获得自杀患者的批准是不可理喻的。”
它未被批准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医学上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制药公司进行了数百项试验,测试至少10种抗抑郁药以治疗严重的经前综合症、社交焦虑症和其他各种疾病。他们几乎从未在最重病的人身上测试他们的药物,那些濒临自杀的人。有伦理考虑:医生不想给一个即将自杀的人服用安慰剂。而且还有声誉方面的担忧:药物试验中的自杀可能会影响药物的销售前景。
在美国自杀疫情中,风险与收益的计算发生了变化。 从1999年到2016年,自杀率增加了30%。现在它是10到34岁人群中第二大死亡原因,仅次于意外。(全球情况正好相反:自杀率在下降。)经济差距加大、因战争而受到创伤的退伍军人、阿片类药物危机、轻易获得枪支——这些都被认为是美国自杀率上升的原因。缓解这些情况的突破尚未出现。
但最终,确实有一个对自杀治疗的严肃探索。氯胺酮处于中心位置,关键是制药行业现在看到了一个路径。来自 强生的首个基于氯胺酮的药物,可能在三月获得对抗治疗抵抗性抑郁症的批准,并在两年内针对自杀思维。 艾尔根制药在开发自己的快速作用抗抑郁药方面也不甘落后,这可能有助于自杀患者。这一切的发生是近期科学研究中最令人振奋的故事之一。
 丹尼斯·查尼在西奈山医院。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为《彭博商业周刊》拍摄丹尼斯·查尼,纽约西奈山医院艾坎医学院的院长,工作在一个充满家庭照片、文凭和长期研究生涯奖项的办公室里。墙上的一件东西与其他的不同:一项关于将氯胺酮的鼻用喷雾形式作为自杀患者治疗的专利。这种药物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查尼职业生涯的故事。
丹尼斯·查尼在西奈山医院。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为《彭博商业周刊》拍摄丹尼斯·查尼,纽约西奈山医院艾坎医学院的院长,工作在一个充满家庭照片、文凭和长期研究生涯奖项的办公室里。墙上的一件东西与其他的不同:一项关于将氯胺酮的鼻用喷雾形式作为自杀患者治疗的专利。这种药物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查尼职业生涯的故事。
在1990年代,他是一名精神病学教授,指导当时的副教授约翰·克里斯塔尔在耶鲁大学,试图弄清楚血清素的缺乏如何影响抑郁症。那时,抑郁症研究全都围绕血清素。1987年,首个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百忧解的批准,开启了一个行业内称为“我也药物开发”的时代,这种研究 旨在改善现有药物,而不是探索新方法。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制药公司不断推出一款又一款的畅销药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2011年至2014年间进行的一项 调查,每八名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报告在过去一个月内使用过抗抑郁药。
查尼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克里斯塔尔对精神分裂症感兴趣。他们的好奇心将他们引向同一个地方:谷氨酸系统,克里斯塔尔称之为“高级大脑的主要信息高速公路”。(谷氨酸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帮助脑细胞进行交流。它被认为在学习和记忆形成中至关重要。)他们已经使用氯胺酮暂时产生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以更好地理解谷氨酸在该病症中的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他们决定在耶鲁大学附属的康涅狄格州退伍军人医疗系统进行一次单剂量的氯胺酮研究,招募九名患者(最终有两名退出),以观察抑郁症患者对该药物的反应。
“如果我们做了典型的事情……我们将完全错过抗抑郁效果”
在麻醉学领域之外,氯胺酮的知名度,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因为其滥用潜力。街头使用者有时会服用足够大的剂量以进入所谓的“K洞”,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无法与周围的世界互动。在一天的时间里,这些娱乐性剂量可能是查尼和克里斯塔尔计划给患者的微小剂量的100倍。然而,他们决定监测患者72小时——远远超过氯胺酮产生明显行为效应的两个小时——只是为了小心不遗漏可能出现的任何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药物测试的典型做法,”克里斯塔尔说,“我们将完全错过氯胺酮的抗抑郁效果。”
在药物施用四小时后检查患者时,研究人员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令我们惊讶的是,”查尼说,“患者开始说他们感觉好些了,他们在几小时内感觉好些了。”这在医学上是前所未闻的。抗抑郁药通常需要几周或几个月才能见效,而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并未得到足够的帮助。“我们感到震惊,”克里斯塔尔说,他现在担任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我们没有在几年内提交结果以供发表。”
当查尼和克里斯塔尔在2000年发表他们的 研究结果时,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也许是因为试验规模太小,结果几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或者可能是因为氯胺酮作为一种非法药物的声誉。又或者是副作用,这一直是个问题:氯胺酮可能导致患者产生解离感,意味着他们进入一种感觉心灵和身体不再连接的状态。
但可能没有这些因素比赤裸裸的经济现实更重要。制药行业并不打算花费数亿美金进行对像氯胺酮这样旧而便宜的药物的大规模研究。氯胺酮最初是作为一种比麻醉剂苯环利定(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PCP或天使尘)更安全的替代品开发的,自1970年以来一直获得批准。即使科学家发现了全新的用途,开发一种已经过了专利期很久的药物也很少能获利。
尽管有这些包袱,关于氯胺酮的研究仍然缓慢推进。那项几乎未被发表的小型研究现在已被引用超过2000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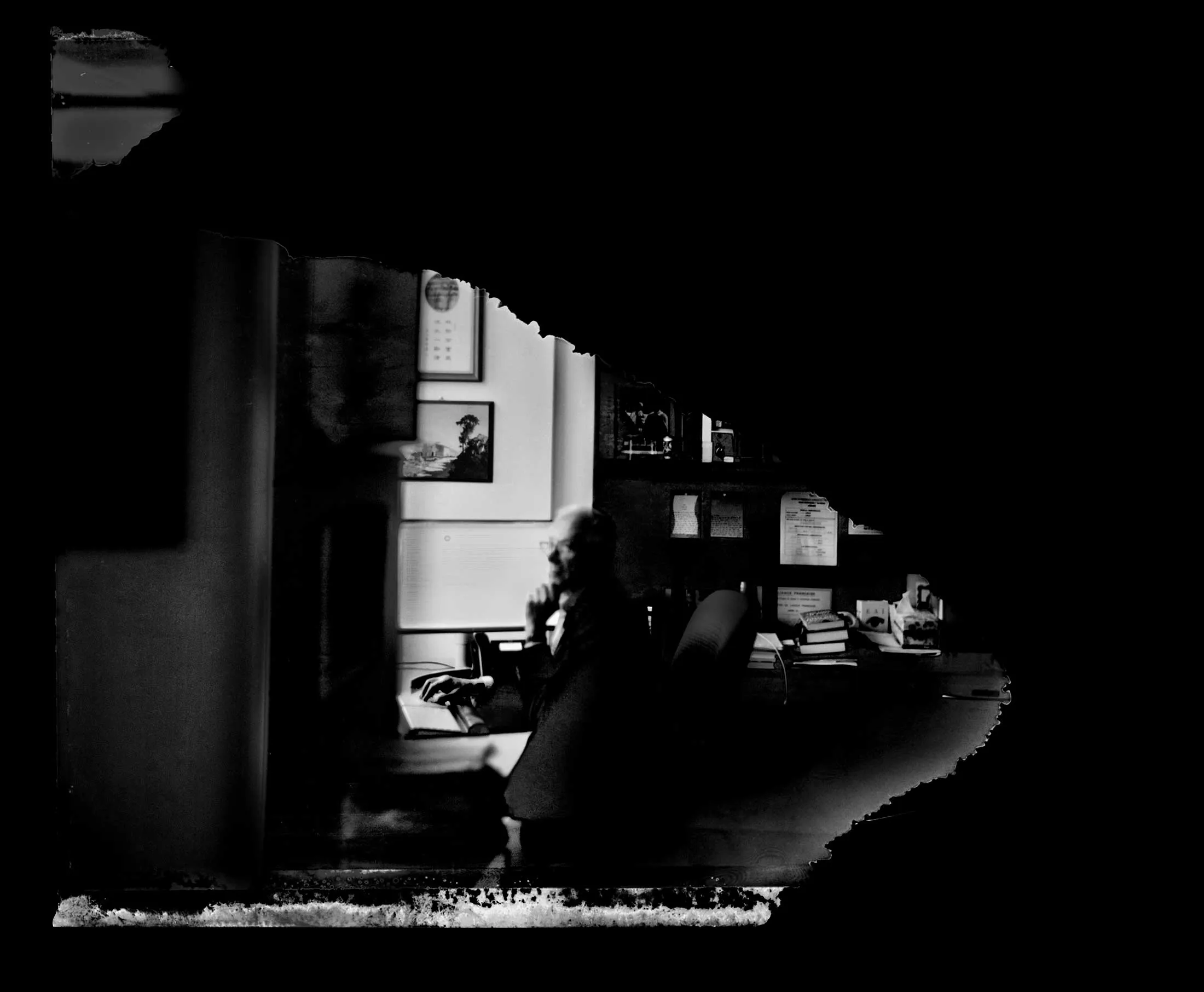 约翰·曼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精神病研究所的办公室。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为《彭博商业周刊》拍摄自杀在医学上被描述为由多种心理障碍和困境引起的——这是一个有许多可能根源的悲剧。严重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情况被认为是已知的风险因素。童年创伤或虐待也可能是一个因素,可能还有遗传风险因素。
约翰·曼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精神病研究所的办公室。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为《彭博商业周刊》拍摄自杀在医学上被描述为由多种心理障碍和困境引起的——这是一个有许多可能根源的悲剧。严重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情况被认为是已知的风险因素。童年创伤或虐待也可能是一个因素,可能还有遗传风险因素。
基于这些事实,约翰·曼,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精神科医生,拥有神经化学博士学位,做出了一个飞跃。他假设,如果自杀有许多原因,那么所有自杀的大脑可能有某些共同特征。此后,他进行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工作,以阐明研究人员所称的自杀生物学。这个短语本身代表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存在一种潜在的生理易感性与自杀相关,除了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之外。
曼于1978年移居纽约,并在1982年于康奈尔大学开始收集自杀者的大脑。他招募了维多利亚·阿兰戈,现在是自杀生物学领域的领先专家。研究尸检脑组织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流行,曼希望重新启动这一做法。“他非常自豪地带我去冰箱,”阿兰戈回忆起曼向她介绍大脑收藏的那一天,当时大约有15个。“我说,‘我该怎么处理这个?’”
 曼的脑部收藏的一部分。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彭博商业周刊他们首先将这些工作和脑组织带到了匹兹堡大学,然后在1994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现在已经积累了大约1000个人脑的收藏——一些来自自杀受害者,其他的是对照脑——整齐地存放在保持在-112华氏度的冰箱中。小巴尔干国家马其顿贡献了最新的脑组织,这要感谢一位来自那里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帮助安排了这一切。马其顿的脑组织在被移除后立即冷冻,并通过行李箱运输,陪同人员护送,跨越约4700英里,最终装在鞋盒大小、带有二维码的黑色盒子里。里面是用塑料袋装的粉色组织切片,标记着:右侧、左侧、采集日期。
曼的脑部收藏的一部分。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彭博商业周刊他们首先将这些工作和脑组织带到了匹兹堡大学,然后在1994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现在已经积累了大约1000个人脑的收藏——一些来自自杀受害者,其他的是对照脑——整齐地存放在保持在-112华氏度的冰箱中。小巴尔干国家马其顿贡献了最新的脑组织,这要感谢一位来自那里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帮助安排了这一切。马其顿的脑组织在被移除后立即冷冻,并通过行李箱运输,陪同人员护送,跨越约4700英里,最终装在鞋盒大小、带有二维码的黑色盒子里。里面是用塑料袋装的粉色组织切片,标记着:右侧、左侧、采集日期。
在1990年代初,曼和阿兰戈发现自杀的抑郁患者在大脑某些区域的血清素有微妙的变化。曼记得与阿兰戈和她的丈夫、长期研究伙伴神经生理学家马克·安德伍德一起坐着,分析受缺陷影响的大脑部分。他们努力理解这一点,直到他们意识到这些正是著名精神病案例研究中描述的相同大脑区域。1848年,美国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在他工作的炸药意外爆炸时,被一根43英寸长的夯铁刺穿了头骨。他幸存下来,但他的个性发生了永久性改变。在一篇题为“从铁棒穿过头部的恢复”的论文中,他的医生写道,盖奇的“动物倾向”显现出来,并形容他使用“最粗俗的脏话”。现代研究表明,夯铁破坏了大脑中与抑制相关的关键区域——这些区域在自杀的抑郁患者中也发生了变化。对这个团队来说,这是一个线索,表明自杀患者大脑的差异在解剖上是重要的。
 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阿兰戈。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彭博商业周刊“大多数人抑制自杀。他们找到不去做的理由,”安德伍德说。由于大脑中通常控制抑制和自上而下控制的部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杀的人“找不到不去做的理由,”他说。
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阿兰戈。摄影师:马克斯·阿吉莱拉-赫尔维格,彭博商业周刊“大多数人抑制自杀。他们找到不去做的理由,”安德伍德说。由于大脑中通常控制抑制和自上而下控制的部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杀的人“找不到不去做的理由,”他说。
大约八年前,曼看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氯胺酮研究蓬勃发展,并将这种药物加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在一项试验中,他的团队发现氯胺酮治疗能够在24小时内比对照药物更有效地缓解自杀念头。关键是,他们发现氯胺酮的抗自杀效果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该药物的抗抑郁效果,这有助于支持他们的论点,即自杀冲动不一定只是抑郁的副产品。正是这项由曼的同事迈克尔·格鲁内鲍姆领导的研究,使乔·赖特成为了信徒。
“就像你肩上有50磅的重担,而氯胺酮让你减轻了40磅。”
在200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聘请查尼负责情绪障碍和实验药物研究。这是他推进氯胺酮研究的完美场所。在那里,他进行了复制他和耶鲁大学同事发现的工作的研究。在一项研究中,2006年由研究员卡洛斯·扎拉特领导,扎拉特现在负责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氯胺酮和自杀倾向的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团队发现患者在两小时内从单剂量药物中获得了“强烈和快速的抗抑郁效果”。“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在前几个受试者中,我们想,‘哦,你总能找到一个或两个好转的患者,’”扎拉特回忆道。
在一项2009年的研究中,西奈山医院的患者在治疗抵抗性抑郁症方面,在24小时内显示出自杀思维的快速改善。次年,Zarate的团队在40分钟内证明了抗自杀的效果。“你能够复制这些发现,这些快速的发现,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Zarate说。
最终,氯胺酮重新进入了商业药物开发。2009年,强生公司挖走了Husseini Manji,这位曾在该药物上工作的著名NIH研究员,来负责其神经科学部门。强生并没有明确雇佣他来将氯胺酮开发成新药,但在他任职几年后,Manji决定对此进行研究。这次将以一种氟氯胺酮的鼻用喷雾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化学结构相近的药物。这将允许获得专利保护。此外,鼻用喷雾消除了静脉注射形式所带来的一些挑战。精神科医生通常没有设备在办公室内施用静脉药物。
在这些进展缓慢的同时,一些医生——主要是精神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采取了行动。大约在2012年,他们开始开设氯胺酮诊所。现在在主要城市地区已经出现了数十家。这些中心通常不接受保险,但人们可以支付约500美元进行药物输注。曾几何时,这是一种文化现象——2015年一篇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称其为“俱乐部药物疗法。”自那时以来,新奇感已经消退。今年九月,美国氯胺酮医生协会召开了关于该药物非常规使用的首次医学会议。
“你们真的在拯救生命,”麻醉师转行成为氯胺酮提供者的史蒂文·曼德尔对大约100人(主要是医生和护士执业者)说,他们聚集在奥斯汀,听他和其他早期采用者谈论他们如何使用这种药物。演讲者在讲述其有效性的轶事时,偶尔会被欢呼声打断。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个 共识声明 在 JAMA Psychiatry 2017年发布,表示对氯胺酮使用“迫切需要一些指导”。作者特别关注缺乏关于该药物在情绪障碍患者中长期使用安全性的数据,指出医学界对其长期影响存在“重大空白”。
氯胺酮的非标签使用背景是精神病治疗的缩小空间。自1960年代开始的美国精神健康系统去机构化努力,几乎导致精神病医院甚至普通医院内精神病床位的消失。根据 治疗倡导中心 的数据,2016年州医院中有37,679张精神病床位,而1955年为558,922张。如今,一个人在自杀未遂后常常在几天内就被出院,这造成了一个风险情况,即可能尚未完全康复的人回到家中,手里拿着一堆可能需要数周才能改善情绪的抗抑郁药,如果它们有效的话。
氯胺酮诊所可以成为这种情况的出路——对于有条件和能力的人来说。对于53岁的缅因州居民达娜·曼宁来说,她患有双相情感障碍,500美元的费用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我每天都想死,”她说。
在2003年,她尝试通过服用包括安定和止痛药在内的药物过量自杀,曼宁几乎尝试了所有批准用于双相情感障碍的药物。没有一种能阻止情绪波动。2010年,抑郁症再次袭来,强烈到她几乎无法起床,不得不辞去医疗记录专员的工作。电休克治疗,这种针对不响应药物的抑郁患者的最后手段,也没有帮助。
她的精神科医生深入医学文献寻找治疗方案,最终建议使用氯胺酮。她说,他甚至能够让州医疗补助计划为此报销。她在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之前接受了四次每周的输注,那里的家人更多,可以照顾她。
她说,接受氯胺酮治疗后的前几周是“15年来我唯一能说感觉正常的时刻”。“就像你肩上有50磅的重担,而氯胺酮让你减轻了40磅。”
她现在回到缅因州,抑郁症又回来了。她目前的医疗保险不覆盖氯胺酮。她每月靠1300美元的残疾收入生活。“知道它在那里而我却无法得到,令人无比沮丧,”她说。
 马克·安德伍德在纽约州精神病研究所。摄影师:Max Aguilera-Hellweg 为彭博商业周刊氯胺酮被科学家视为一种“肮脏”的药物——它同时影响大脑中的许多通路和系统,因此很难单独找出它在帮助某些患者时有效的确切原因。这是研究人员继续寻找更好版本药物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新版本可以申请专利。如果强生的氟氯胺酮上市,氯胺酮的开创者及其研究机构将受益。耶鲁大学的克里斯塔尔、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扎拉特和西奈山的查尼,所有这些人都在查尼的专利墙上,将根据药物的销售收取版税。强生尚未透露潜在的定价,但有充分理由相信,自百忧解以来抑郁症治疗的最大突破将会很昂贵。
马克·安德伍德在纽约州精神病研究所。摄影师:Max Aguilera-Hellweg 为彭博商业周刊氯胺酮被科学家视为一种“肮脏”的药物——它同时影响大脑中的许多通路和系统,因此很难单独找出它在帮助某些患者时有效的确切原因。这是研究人员继续寻找更好版本药物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新版本可以申请专利。如果强生的氟氯胺酮上市,氯胺酮的开创者及其研究机构将受益。耶鲁大学的克里斯塔尔、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扎拉特和西奈山的查尼,所有这些人都在查尼的专利墙上,将根据药物的销售收取版税。强生尚未透露潜在的定价,但有充分理由相信,自百忧解以来抑郁症治疗的最大突破将会很昂贵。
该公司的初步氟氯胺酮研究涉及68名高风险自杀患者。为了避免对在积极自杀的受试者使用安慰剂的担忧,每个人都接受了抗抑郁药和其他标准治疗。大约40%的接受氟氯胺酮的患者在24小时内被认为不再有自杀风险。目前正在进行两个更大规模的试验。
当强生 在美国精神病学会会议上公布其氟氯胺酮研究的数据时,演示会座无虚席。氟氯胺酮可能成为首个快速起效的抗抑郁药,医生和投资者都在渴望了解它的工作原理。自杀患者的结果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可能 为2020年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自杀抑郁患者使用的申请铺平道路。艾尔健预计明年也将有其自杀研究的结果。
“事实是,大家关心的就是,他们是否减少了自杀尝试?”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研究员格雷戈里·西蒙说,来自凯瑟 Permanente 华盛顿健康研究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回答,并且我们正在为这些治疗方法的可用性做准备。”
氯胺酮及其同类药物艾司氯胺酮的具体作用机制仍然是激烈辩论的主题。实质上,这些药物似乎为因压力或抑郁而受损的脑提供了一个快速的分子重置按钮。氯胺酮和艾司氯胺酮都释放出一阵谷氨酸。这反过来可能会触发大脑中与情绪和感受快乐能力相关的区域的突触或神经连接的生长。药物可能通过增强这些电路,同时重新建立一些防止一个人自杀所需的抑制作用来防止自杀。“我们当然认为艾司氯胺酮正好作用于抑郁的电路,”曼吉说。“我们是否准确锁定了自杀意念所在的位置?”他在NIH的前同事们也在努力寻找大脑中的那个点。通过多导睡眠图——患者头部各个部分连接节点以监测脑活动的睡眠测试——以及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扫描),研究人员可以观察患者的大脑如何对氯胺酮作出反应,以更好地理解它究竟是如何抑制自杀思维的。
关于氯胺酮类药物副作用的担忧依然存在。一些服用艾司氯胺酮的患者报告经历了解离症状。强生公司称这些效果是可控的,并表示它们在治疗后一个小时内出现,此时服用药物的人可能会被留在医生办公室进行监测。一些患者在同一时间段内也经历了血压的适度上升。
鼻用喷雾剂的剂量带来了其他问题。澳大利亚的黑狗研究所和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联合研究了一种鼻用喷雾形式的氯胺酮,并于去年三月在心理药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发现患者之间的吸收率存在差异。强生公司表示,其自身对氟氯胺酮的研究与这些发现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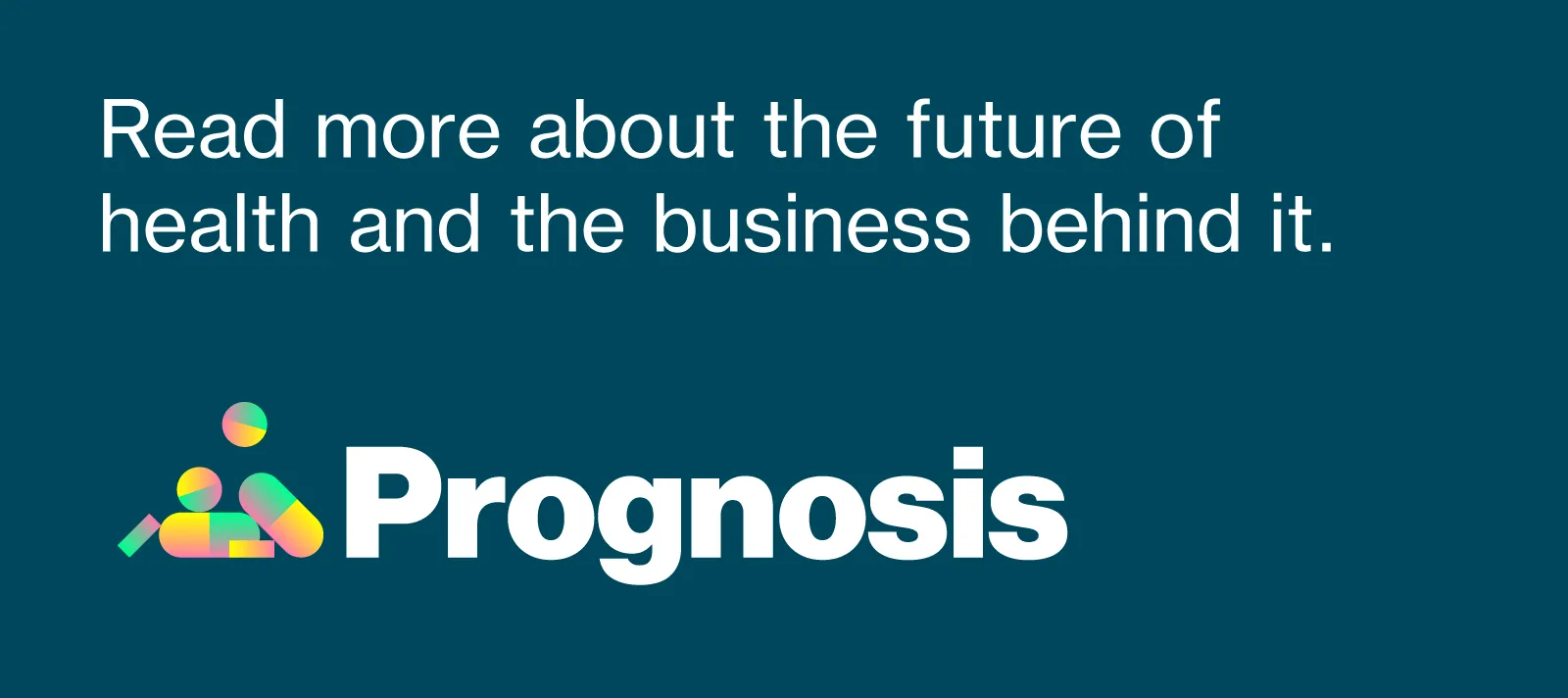 但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之后,也许最大的担忧是,过度放松对氯胺酮和类似药物使用的限制可能会导致新的滥用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分析师对艾尔健的快速作用抗抑郁药rapastinel特别感到兴奋,因为它在测试中比氟氯胺酮晚了一年。研究人员表示,它可能作用于大脑中与氯胺酮相同的靶点,即NMDA受体,但以更微妙的方式,可能避免解离副作用和滥用潜力。艾尔健副总裁阿尔敏·塞格迪表示,实验动物的研究表明,该药物不会导致生物体寻求更多的药物,正如它们有时会对氯胺酮那样。艾尔健的药物是一种静脉注射药物,但该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口服药物。
但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之后,也许最大的担忧是,过度放松对氯胺酮和类似药物使用的限制可能会导致新的滥用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分析师对艾尔健的快速作用抗抑郁药rapastinel特别感到兴奋,因为它在测试中比氟氯胺酮晚了一年。研究人员表示,它可能作用于大脑中与氯胺酮相同的靶点,即NMDA受体,但以更微妙的方式,可能避免解离副作用和滥用潜力。艾尔健副总裁阿尔敏·塞格迪表示,实验动物的研究表明,该药物不会导致生物体寻求更多的药物,正如它们有时会对氯胺酮那样。艾尔健的药物是一种静脉注射药物,但该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口服药物。
为了进行自杀研究,艾尔健正在努力招募退伍军人,这是最近自杀激增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并已将多个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纳入试验地点。根据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6年,每年有超过6000名退伍军人自杀,这一比例比一般人群高出50%,即使在调整人口统计数据后也是如此。
“大脑如何调节我们是谁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Szegedi说。“真正改变这里局面的,是你有临床数据表明‘这确实有效。’一旦你在黑暗中发现了某些东西,你真的必须弄清楚:你能做得更好、更快、更安全吗?”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有自杀念头,国家自杀预防热线是1 (800) 273 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