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联邦主义中重新确认城市权力 - 彭博社
bloomberg
 工人们在联邦大厅博物馆前为乔治·华盛顿雕像搭建脚手架。卢卡斯·杰克逊/路透社这篇文章是 CityLab 关于权力的系列*——政治权力、电池和油箱里的东西,以及群众运动的变革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城市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们 推动经济,孕育文化和新思想,并集中人类才华。
工人们在联邦大厅博物馆前为乔治·华盛顿雕像搭建脚手架。卢卡斯·杰克逊/路透社这篇文章是 CityLab 关于权力的系列*——政治权力、电池和油箱里的东西,以及群众运动的变革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城市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们 推动经济,孕育文化和新思想,并集中人类才华。
然而,在美国,城市严重缺乏政治权力。选举人团和国会选区的选区划分限制了城市选票的国家影响力,我们的联邦制几乎不承认城市政府做出独立决策的权利。虽然各州可以引用第十修正案来挑战联邦政府,但城市没有类似的法律机制。没有宪法或政策工具来抵抗联邦侵占或设定地方优先事项,城市必须发挥创造力,推翻对其政治权力的传统假设。
彭博社CityLab美国人如何投票导致住房危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转学生提供专门建造的校园住所熊队首席警告芝加哥在没有新NFL体育场的情况下面临风险罗马可能开始对特雷维喷泉收取入场费这是理查德·施拉格尔在 城市权力:全球时代的城市治理 中提出的论点,他是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法律教授。他通过电话与CityLab交谈,讨论大都市地区如何绕过这些结构性挑战,并重新发挥其影响力。
您在选举发生之前写了这本书。自那时以来,我们听到了更多关于美国城市必须在联邦主义系统中重新assert权力的声音。选举对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有影响吗?
它强化了书中关于将权力去中心化到城市的论点。特朗普的当选揭示了美国农村和郊区与城市之间的巨大政治分歧,这种分歧在过去20到25年的城市复兴中被加剧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的繁荣和活力加剧了城市中的国际化人士与我所称的城市外的传统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似乎并没有消失。当你查看政治地图时,它们非常明显——不是蓝州和红州,而是蓝色城市和大都市地区与红州。
城市拥有如此多的经济活力和大量的人口——为什么这没有转化为更多的政治权力?
城市确实可以并且能够行使某些经济和监管权力。我们在城市复兴中看到了经济权力的进一步增强。问题出在我们的州为基础的联邦制度中。州立法机构和州官员限制了城市的行动能力。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优先权危机——当州政府推翻他们不喜欢的地方法律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通过他们的跨性别浴室法时,州立法机构介入,不仅推翻了该法律,还通过了一项优先权法,推翻了最低工资、地方合同规则以及各种地方反歧视法律。
“市长应该少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而更多关注为现在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基本服务。”在佛罗里达州,他们通过优先立法威胁地方官员被免职,我称之为惩罚性优先权。在塔拉哈西,这是一个关于地方枪支监管的案例。那一案例中有特别尖锐的优先权。 你会看到州政府对进步地方立法的巨大反对。城市拥有经济权力,通常是其地区的经济驱动力——坦率地说,也是他们的州——但他们常常受到州立法机构的限制。
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关键点是,城市是经济引擎,但资本本质上可以在不同地方流动。城市如何利用他们的经济权力来推动政治变革?
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城市必须参与联盟建设。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城市可以通过尝试与商业建立联盟来做到这一点。北卡罗来纳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商业社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反对州政府推翻地方跨性别者浴室条例。
城市还可以努力选举州级官员,特别是对他们的政治议程持同情态度的州长。城市在州级选举中更有可能行使权力,而不是在州立法机构中,后者的个别成员不会受到城市经济实力的影响。
在书中,你引用了林登·约翰逊关于总统职位的著名玩笑:“情况可能更糟。我可能是一个市长。”我们需要了解市长的权力吗?
我认为市长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被低估了,因为权力往往向上移动。但市长在这个国家承担了许多治理的艰巨工作。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州官员与市长竞争政治功劳,并且他们常常将政治责任转嫁给市长。当州长和州立法机构推动减税时,这些减税的负担往往落在地方服务上。然后地方必须弥补不足。州立法者和国家立法者与市长等地方官员处于政治竞争中。这种政治竞争意味着官员们会推翻他们不同意的地方努力,而他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还有另一个问题:市长通常被视为城市的首席执行官。我们认为城市是市长经营的企业。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就期望市长促进经济发展。市长和城市官员应该少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相反,他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为现在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基本服务。与其试图吸引新的人和企业来到你的城市,不如尽力为现在居住在那里的居民提供服务。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哪些政策在促进城市增长方面是有效的。我们应该在城市中提供资源去做正确的事情,即使我们不确定这是否会促进增长。
我们国家需要的一件事是更强大的跨城市政治运动。城市应该将自己视为有共同利益的机构,并联合起来。竞争城市能否合作以增强它们的共同利益?
我们应该拒绝城市之间竞争的想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竞争,尽管人们确实倾向于这样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并且这种思维方式对城市的力量造成了损害。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认识到城市的共同利益。我们开始表现得好像这是零和游戏——这个城市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而那个城市则没有。这不是区域经济运作的方式。经济地理学家表明,这不是关于竞争——而是关于城市在其他城市的背景下以及这些城市之间的贸易背景下运作的聚集经济。
一旦我们抛弃竞争范式,我们就可以开始更多地思考城市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我们国家需要的一件事是更强大的跨城市政治运动。城市应该将自己视为有共同利益的机构,并联合起来。我们现在没有那种政治运动。
另一个浮现到联邦层面的问题是经济不平等,而在城市中,这种不平等变得非常明显。城市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权力,尤其是当一些经济最成功的大都市往往也有最高的不平等水平时?
城市是创造财富的有效工具,而这些财富往往分配不均。城市可以做的是改善不平等。当地最低工资运动在这个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城市在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再分配方面的参与超出了理论家的想象。
城市可以为工人阶级和移民提供机会,使他们进入中产阶级。这正是城市在20世纪初所做的,城市可以再次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为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教育、交通安全和医疗保健。这些事情可以由城市提供。这就是城市在新政时代所做的。曾经有一股力量来安置、喂养、穿衣和照顾城市公民。城市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并且可以做得更多。
但做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联邦资金。随着特朗普政府提议削减城市住房和交通的资金,城市应该如何处理联邦主义的问题,并为这些基本项目而奋斗,尤其是当城市在联邦税收中支付如此之多时?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有很多联邦资金支持城市所做的事情,比如支持反贫困项目或交通。现在我们有一个对社会福利国家持敌对态度的政府。不幸的是,城市可能不得不承担这些削减和成本。城市中有资源的人需要倡导和推动更好的资源分配,以便在政治上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城市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照顾自己的任务。这将对他们的资源造成一些压力。这意味着希望看到这些政策的人必须在地方层面上进行,而不是期待联邦政府的支持。
这很困难,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依赖联邦政府支持的进步思想者。更好的策略是在地方层面获得支持,并在城市层面追求这些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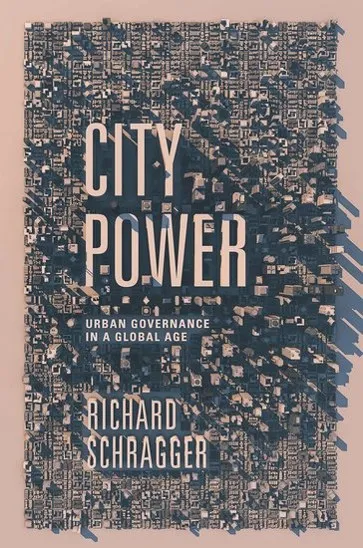 哪些城市提供了这一策略的良好示例?
哪些城市提供了这一策略的良好示例?
有些城市正在进行我所称之为进步政策制定的工作。旧金山就是一个劳动友好的城市,纽约市也是一个例子。但也有一些较小的城市在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在书中,我谈到了社区利益协议,这是一种利用地方权力更广泛地分配发展成本和收益的方法。底特律正在试验社区利益协议。我在书中谈到了纽黑文的一个例子。洛杉矶试图利用其对洛杉矶港的控制来采用环保和劳动友好的法规。不幸的是,[环保法]在联邦法院受到挑战,并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这是一个地方努力追求政策却被联邦或州法律关闭的例子。
由于城市在这个国家因结构原因处于政治弱势地位,抵抗这一点只能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既是诉讼答案又是具体政策答案的解决方案。美国的城市需要作为城市做出回应。它们必须建立抵制资金撤回、惩罚性优先权和覆盖地方立法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