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知识分子奇葩如何重塑了从医学到投资的一切 - 彭博社
Drake Bennett
 作者:迈克尔·刘易斯
作者:迈克尔·刘易斯
摄影师: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仅仅因为迈克尔·刘易斯非常擅长解释事物,并不意味着他总是想要这样做。因此,当他在写一本书时,他会想出一些令人畏惧的无聊方式来谈论它。“哦,一本关于棒球统计的书,”他会说,或者“一本关于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的书,”而这段对话,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结束了。“没有人再问另一个问题,”他说。
这些描述并没有错。但刘易斯的伟大天赋在于能够将看似枯燥的主题转化为令人振奋的智力冒险,随着情节的发展,金融衍生品或棒球指标的复杂性被逐步揭示。然而,他的最新书籍却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用一种结束对话的方式来说,它是关于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的。在19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颠覆了我们对人类判断和决策的理解,展示了影响我们成本和收益计算的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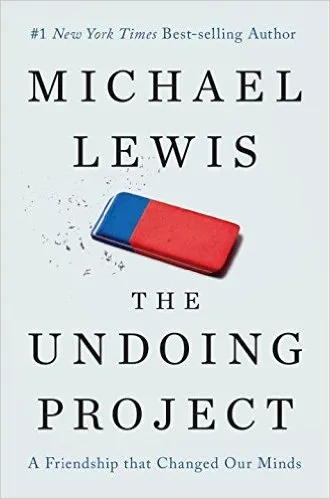 来源:W. W. Norton & Company刘易斯在他的新书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解构项目》,作为一种不太可能且最终注定要失败的智力浪漫:特沃斯基大胆而迷人,卡尼曼自我怀疑且情绪多变。在这两位男士在希伯来大学共度的十年里,他们每天花费数小时进行即兴表演和开玩笑,互相抛出想法,并提出奇特而揭示性的问题来询问他们的受试者。字母K更可能是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还是第三个字母?你更愿意有50%的机会赢得1000美元,还是选择确保获得400美元?人们的回答揭示了一系列心理捷径以及它们可能导致的奇怪地方:事实证明,我们对容易想象的事物赋予了过多的权重,厌恶损失超过我们对收益的喜爱,并且关注变化,而不是总数。
来源:W. W. Norton & Company刘易斯在他的新书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解构项目》,作为一种不太可能且最终注定要失败的智力浪漫:特沃斯基大胆而迷人,卡尼曼自我怀疑且情绪多变。在这两位男士在希伯来大学共度的十年里,他们每天花费数小时进行即兴表演和开玩笑,互相抛出想法,并提出奇特而揭示性的问题来询问他们的受试者。字母K更可能是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还是第三个字母?你更愿意有50%的机会赢得1000美元,还是选择确保获得400美元?人们的回答揭示了一系列心理捷径以及它们可能导致的奇怪地方:事实证明,我们对容易想象的事物赋予了过多的权重,厌恶损失超过我们对收益的喜爱,并且关注变化,而不是总数。
彭博社商业周刊不是囚犯。寻求庇护者占据了拜登承诺关闭的监狱美国正在用寻求庇护者填满臭名昭著的前监狱大学橄榄球需要向大联盟学习一课销售比职业选手更多棒球棒的网红兄弟们他们并肩坐在一台打字机前,起草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将重塑从投资到体育再到医学和管理的一切。2002年,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沃斯基无疑也会获奖,如果他没有在几年前死于癌症)。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工作为许多最终引起刘易斯注意的特立独行者奠定了基础。这位作者是 彭博观点的专栏作家,他在其出版商W.W. Norton的办公室坐下来谈论这一点。采访经过压缩和编辑以提高清晰度。
彭博商业周刊**: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工作的核心洞察是什么?**
**迈克尔·刘易斯:**我们被编程为错误。并不是说有些人犯错误而有些人不犯。大脑被编程为犯某些类型的错误,某些类型的系统性误判。大脑是易错的,这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我会说第二个相关的想法——也许是导致易错性的原因——是大脑所做的事情之一是让世界看起来比实际更确定。人们很难接受或承认在任何给定时刻世界的实际不确定性。因此,大脑编造故事,使世界看起来更加确定。
但是我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小见解令人惊叹:刻板印象扭曲判断的力量,人们对损失的敏感程度高于对收益的敏感程度。还有人们对事物的描述的反应,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反应。我发现那些有点未完成的东西同样有趣,他们只是随意探讨。
我想如果有人问我,“我为什么要读你的书?”我不会说是因为你需要了解他们的工作。我会说你需要了解 他们。你需要在脑海中深深印下他们的印记,以便你可以问自己,“我想知道阿莫斯·特沃斯基会怎么说这个,或者丹尼·卡尼曼会怎么说这个。”这真的很丰富。
是的,你的书名是对他们一些后期工作的引用[关于想象和遗憾],而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东西。
想象有规则的这个想法,真是一个惊人的见解。因为你不会把它视为一种基于规则的活动。但它确实是。当人们被迫想象一个替代场景,比如唐纳德·特朗普可能是如何失败的,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直接想到可能改变结果的最后一件事,然后做一些简单、生动的事情。比如他们记得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或其他什么。他们不会说,“要是特朗普出生是个女孩就好了。”
我认为他们工作的一个主题是人类想象力的局限性。我们把它视为这种美妙的苹果广告那样的东西——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想到任何事情,对吧?但想想现在人们在提供对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想象性看法时遇到的麻烦。他们回忆起他们记得的东西,比如,“哦,也许是希特勒。”那是想象力的失败。很可能会是我们都没有想象过的东西。而且会很疯狂。我们所有人都有的不确定感就是那种:我们无法完全想象它。
这两个家伙是以色列人是否重要?他们必须是吗?以色列有什么东西塑造了他们的想法吗?
将决定论模式强加于他们的故事是忽视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教训。但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在大屠杀之后,随着以色列国家的诞生,犹太人被敌人包围,对判断和决策特别感兴趣,因为错误的判断可能是致命的。我认为希特勒的错误判断在背后。
以色列迫使这些人以知识分子通常不这样做的方式与社会互动。他们必须参加军事行动。每隔几年,他们就会被召回进行后备役,大家都期待他们能有所作为。因此,如果你见到丹尼·卡尼曼并了解他,如果他只是留在法国而二战没有发生,他本来会是一个与周围世界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而以色列迫使他变得有用。一旦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有用,这种感觉就变得令人陶醉。
我喜欢书中关于以色列军队单位嵌入心理学家的细节。
关于这方面的论文非常搞笑。我是说,谁会这样做?本尼·沙利特(以色列军事心理学负责人)有这些想法,认为心理学家将在战场上实时有效地做出决策。我是说,这太疯狂了。
无论你在哪里看,专家的直觉判断正在退却,他们都发挥着作用,甚至在华尔街。
显然,吸引你的部分原因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在你的描述中,这似乎是列侬和麦卡特尼与婚姻的结合。
是的。这在书中没有提到,但他们一起旅行时,有几次酒店的人确信他们是同性恋。而他们并不是。我是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直男,但他们对彼此的感情比对其他人、比对他们的妻子要强烈得多。我认为这一点很明显。
你认为他们的分手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是如果他们没有离开以色列去美国,他们会一直在一起?
我认为如果他们留在以色列,他们会很好。那里有一种平等的精神,所以他们地位之间的差异——他们并不是一直被提醒这一点。因此,即使阿莫斯比丹尼稍微强势一点,这也没那么重要。
但我不确定他们的作品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被人们所知。如果他们只是几个以色列人,而阿莫斯不是斯坦福大学的名人,与美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互动,我不确定这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关注。话虽如此,你读他们之间的信件,会发现情感上有一种脱节。丹尼有情感需求,而阿莫斯根本不知道如何满足。而反过来并不存在;阿莫斯没有丹尼无法满足的情感需求。很难想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某个时刻没有一些问题。但仅仅看造成关系真正压力的原因,就是他们之间巨大的地位差异,一旦他们来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这些想法的实际应用。[行为经济学家] 理查德·塞勒基于这些内容创办了一个基金,表现还不错,但并不出色。奥巴马政府根据这些想法设计了一项减税政策,试图让人们花钱,而不是存钱,但似乎并没有奏效。
我认为你想得太狭隘了。这是一个应用:指数基金。我的意思是,整个市场已经不再依赖选股了。显然,这不仅仅是丹尼和阿莫斯的贡献,就像基于证据的医学不仅仅是丹尼和阿莫斯的贡献一样。但是如果你回去和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的人谈谈,他们在推动医生不应凭直觉做出诊断,应该对诊断进行某种数据库检查,你和他们交谈时,他们会说,‘我们深陷于他们的工作中。’那项工作在当时对人们解释为什么不能信任专家的直觉判断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无论你在哪里看到专家的直觉判断在退却,他们都发挥着作用,甚至在华尔街。
在棒球中。
体育管理。所有的大数据内容。转向算法的解释是专家的判断存在缺陷。
当你通过阿莫斯和丹尼的视角看特朗普时,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要说,而这些都不愉快。
你在一个这些内容似乎正在上升的时代写了这本书。你有一个智力型的总统,[法律学者] 卡斯·桑斯坦在奥巴马政府中,试图应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想法。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当选总统,更像是一个凭直觉行事的人。
这并不清楚。看看它会发生什么将会很有趣,因为这不仅仅是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德国政府,我是说,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决策的呈现方式影响决策的形成,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它并不天生是自由主义的。
然而,受到威胁的是一种世界观,我们应该都保持某种概率思维。首先,我们应该评估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而不是结果,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结果。
其次,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在世界上行走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我的意思是,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让我们在几年后再谈谈,因为特朗普可能会被赶出城。我是说,这家伙是个小丑。他在回应当下,你知道的。愤怒、性——没有冲动控制。而人们正在拼命创造一个故事,让他看起来像个伟大的战略天才。
他可能会非常幸运。好事可能会发生。我不知道。但毫无疑问,当你通过阿莫斯和丹尼的视角看特朗普时,有很多事情可以说,而没有一件是愉快的。我想说的一个有趣的事情是,那些对自己思维的弱点或脆弱性毫无察觉的人,特别擅长利用他人思维的脆弱性。
你是什么意思?
人们——他们想要比实际可得的更多的确定性,他们会接受,即使这是一种谎言。他们容易被生动的例子操控。你给他们看一个杀了人的非法移民,你就可以说服他们这就是非法移民所做的。这就是[特朗普]的运作方式。他利用人们以刻板印象思考的方式。但我认为他之所以做得如此出色,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思考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抵制,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除了其他事情,这在很多时候是错误的。
但他只是屈服于此,我认为这对那些不想抵抗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这似乎是他吸引力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并不完全是种族主义,对吧?那只是一个副产品。这只是对人们的懒惰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