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1968年,美国警察国家的发明 - 彭博社
bloomberg
 这是一张由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在1968年4月的民事骚乱期间拍摄的照片。詹姆斯·V·凯利/兰斯代尔图书馆特别收藏许多人回顾巴尔的摩1968年圣周起义,以理解本周困扰该市的冲突。但今天的事件与那一年的民事动乱关系不大,更与建立在其废墟上的全国性法治运动有关。
这是一张由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在1968年4月的民事骚乱期间拍摄的照片。詹姆斯·V·凯利/兰斯代尔图书馆特别收藏许多人回顾巴尔的摩1968年圣周起义,以理解本周困扰该市的冲突。但今天的事件与那一年的民事动乱关系不大,更与建立在其废墟上的全国性法治运动有关。
在20世纪伟大的黑人迁移北上过程中,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变化改变了美国城市。结果既有民事动乱,也有对其的保守反弹。在巴尔的摩,起义及其主要批评者,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永远改变了美国政治。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一位艺术家重新构想童年的空间,结果却充满荆棘房地产开发商纳夫塔利在迈阿密海滩寻找交易,推动佛罗里达发展美国的驾驶和拥堵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牙成为全球首个禁止石油和航空旅行广告的城市黑人起义在1960年代中后期席卷美国北部城市。巴尔的摩的起义规模巨大:超过一万名马里兰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军队被派往该市,以平息1968年4月6日爆发的骚乱,这距离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枪杀仅两天。令人震惊的是,超过5000人被逮捕(大多数因违反宵禁),并且在几乎每个主要黑人社区都造成了1200万美元的损失。詹姆斯·布朗的音乐会部分因市民中心成为拘留区而被取消。
在马里兰州,斯皮罗·阿格纽担任州长的反应对全国保守派政治至关重要。破碎的窗户和防暴警察,当时和现在一样,可以通过观看电视报道推测出来。许多人当时看不见的,今天仍然模糊不清的是更深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全国范围内的暴动出现在一个背景下,即伟大社会改革和电视上展示的富裕所承诺的希望与日益加深的城市边缘化相对抗。
“非裔美国人感受到了这一点,”凯斯西储大学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正义研究所主任朗达·Y·威廉姆斯说。“他们也在抵抗。他们正在参与抗议。”
在20世纪中叶,美国城市经历了一场重大的人口革命,黑人美国人从吉姆·克劳南部迁移,联邦政府补贴了仅限白人的郊区发展,而曾经对黑人有希望的工业城市经济(尽管将他们限制在最低工资的工作中)则迁移到了其他地方。
巴尔的摩的白人人口在20世纪后半叶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城市中黑人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郊区的巴尔的摩县见证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从1950年的不到250,000人增加到1970年的600,000人,其中580,000人是白人,约克学院的历史学家彼得·B·莱维说。在城市中,白人社区迅速变成了黑人社区,一个深度隔离的都市,分开且不平等,诞生了。
“在‘68年,巴尔的摩显得极其种族隔离,”莱维说。“而郊区的‘县几乎全是白人。”今天,“它仍然是一个相当隔离的城市,”尽管巴尔的摩县变得更加多样化。根据莱维的说法,在1968年,黑人居民被迫住在破旧的房屋中,接受低标准的教育,某些市中心地区的失业率接近30%。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忽视,贫民区的条件助长了1967年席卷底特律和纽瓦克的巨大骚乱。
“种族隔离和贫困在种族贫民区创造了一个对大多数白人美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破坏性环境,”国家民事骚乱咨询委员会在其1968年关于城市动荡的关键研究中写道,这项研究被称为《凯尔纳报告》。“白人美国人从未完全理解,但黑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是——白人社会与贫民区有着深刻的关系。白人机构创造了它,白人机构维持着它,白人社会对此表示默许。”
与许多南方城市不同,巴尔的摩接受了正式的学校整合,并拥有众多黑人公职人员。其警察部队实际上因在追求对黑人居民的进步方法方面处于前沿而受到赞誉。但巴尔的摩,像北方大都市一样,很快陷入了一种新的美国种族隔离形式,这种形式基于严格的市界限。这并不像站在学校门口那么戏剧化。但其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
“通过法律、房地产、银行实践的技术或工具,以及联邦和地方政策,种族隔离在巴尔的摩得以维持,并受到保护,”威廉姆斯说,她在关于巴尔的摩的书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公共住房的政治:黑人女性对城市不平等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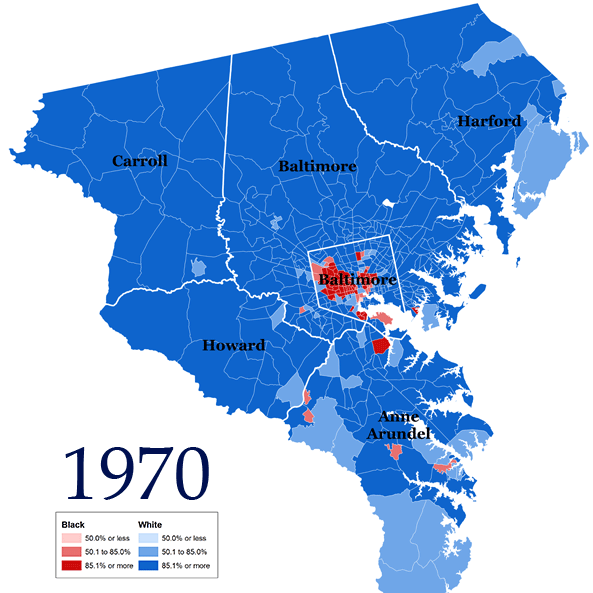 表面上是事实上的隔离,但在其真正基础上是法律上的:政府住房和经济政策。
表面上是事实上的隔离,但在其真正基础上是法律上的:政府住房和经济政策。
“吉姆·克劳在南方以其方式存在,吉姆·克劳在北方以其方式存在,”威廉姆斯说,她是西巴尔的摩的本地人。“我们是一个边界城市。”
四十七年后,黑人总统、黑人市长的选举以及繁忙的内港的经济活力并没有改变巴尔的摩贫困黑人社区许多人的基本生活事实。美国梦与贫民窟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依然存在。
凯尔纳报告在1968年巴尔的摩暴动前仅发布了五周。
“1967年的夏天再次给美国城市带来了种族骚乱,并给国家带来了震惊、恐惧和困惑,”委员会写道。“美国总统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并指示我们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它再次发生?这是我们的基本结论:我们的国家正朝着两个社会发展,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分开且不平等。”
凯尔纳报告是自由主义建立的最后一次伟大努力,陷入日益增长的经济矛盾和越南战争中,试图在不断上升的保守政治潮流淹没之前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但在金恩被刺杀后,巴尔的摩不仅爆发了更多的骚乱,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和匹兹堡也相继发生。马里兰州的反应,斯皮罗·阿格纽担任州长时,将对全国的保守政治产生关键影响。
最初,阿格纽州长对骚乱的反应相对温和。但他很快领导了一场保守的反击,指责激进的煽动者(这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和自由主义滋养了黑人不当行为。阿格纽向右转的时机正值骚乱平息之际,4月11日,他会见了该州的主流黑人领导人,并指责他们怀有“扭曲的种族忠诚观念”,这“激怒了”激进分子。他说,巴尔的摩的火焰并不是“出于压倒性的挫败感和绝望”,而是“在暴力倡导者的建议和指导下点燃的”,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阿格纽在一份值得阅读的声明中全文,对黑人领导人进行了讲解,称“民权运动的目标在情感的过度简化中被模糊”,认为“某种程度上,平等机会的目标已被瞬时经济平等的目标所取代。”阿格纽,这位曾经的温和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将他对巴尔的摩骚乱的批评转化为全国声望,并在理查德·尼克松的领导下担任副总统。
“阿格纽在'68年之前算是一个温和派,”莱维说,他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写作,涉及到起义和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反弹。实际上,“他最初是战胜白人至上主义者当选州长的。”但他对骚乱的反应“将他推向了”全国舞台。“这引起了尼克松和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的注意。他得到了许多保守派的极为积极的反应。”
布坎南实际上最近写道,“阿格纽对在大规模暴力面前沉默的民权领袖们宣读骚乱法令……是尼克松选择他作为副总统的一个主要因素。”
实际上,自由派建立了相对温和的对巴尔的摩起义的反应。在1967年骚乱之后,联邦政府制定了新的“应对城市骚乱的详细程序,”莱维写道,包括“派遣部队,命令他们不得装填武器,并且要避免射击抢劫者。”在巴尔的摩有六人死亡,而1965年在沃茨有34人遇难,1967年在底特律有43人遇难。根据莱维的说法,生命损失较少,主要是因为约翰逊政府的克制反应。
但是阿格纽与保守派联合抨击《凯尔纳报告》,称其将“责任归咎于除了实施者以外的每一个人”,并且“对白人种族主义的自虐式集体罪恶感渗透了报告推理的每一个方面。”他说,骚乱的一个更可能的“间接原因”是“违法行为已成为一种社会可接受且偶尔时尚的抗议形式。”(他还批评了“那些……从甘地那里借鉴战术、从课堂上获取哲学、从父亲那里获取资金的学生的虐待专制。”)
阿格纽在当选州长之前担任巴尔的摩县的执行官,成为了典型的新右派郊区人士。事实上,按照莱维的说法,他是全国首位高调的郊区政治家。阿格纽是尼克松的攻击犬,捍卫尼克松沉默的大多数的理想,反对街头的喧闹少数派,并在他所认为的纵容黑人和学生抗议者的女性化自由主义面前,倡导一种保守的男子气概。对于许多郊区选民来说,他提供了一个比狂热的乔治·华莱士更为冷静的选择。
 马里兰国民警卫队部队回应巴尔的摩1968年的暴动。詹姆斯·V·凯利/兰斯代尔图书馆特别收藏“阿格纽通过打破与公开捍卫吉姆·克劳的关联,帮助合法化了白人反弹,并将其表述为强调秩序、个人责任以及辛勤工作、核心家庭和法律神圣性的语言,”莱维写道。
马里兰国民警卫队部队回应巴尔的摩1968年的暴动。詹姆斯·V·凯利/兰斯代尔图书馆特别收藏“阿格纽通过打破与公开捍卫吉姆·克劳的关联,帮助合法化了白人反弹,并将其表述为强调秩序、个人责任以及辛勤工作、核心家庭和法律神圣性的语言,”莱维写道。
阿格纽自辞职和失宠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正如莱维所见。但在理解新右派和20世纪末法律与秩序政治的过程中,阿格纽和巴尔的摩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骚乱或起义,常常在当下被误解。但它们最具毒性的误表述可能是在事后。1960年代的骚乱被普遍纪念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使美国城市陷入衰退。但实际上,起义大多是结果而非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失业和不平等隔离的结果。(即使是语言也不是中立的,正如你此时可能猜到的那样:学者和活动家寻求强调城市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维度长期以来使用“起义”这个词而不是“骚乱”。
自1960年代以来,警务和监狱(当然还有军队)逐渐成为政府的定义特征。今天也是如此,随着全国各地的黑人抗议者反抗从1960年代末的废墟中崛起的美国警察国家。这并不是在夸张的意义上,执法和司法在一个对法治漠不关心的永久例外状态下运作(尽管它们确实常常如此)。相反,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因为自1960年代以来,警务和监狱(当然还有军队)逐渐成为政府的定义特征。大规模监禁,使如此多的黑人男性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已成为美国居住隔离的一个字面延伸。
“这只是证明人们应该一开始就听从凯尔纳委员会的建议,而不是发起毒品战争和犯罪战争,”莱维说。
在尼克松和阿格纽将法治作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并将白人郊区居民和南方人视为其关键选民后,两党的建制派开始将城市危机和生活在其中的边缘化黑人视为一个更好被忽视或锁在监狱里的问题。“这怎么会发生?”一位年轻的国民警卫队员在1968年警察执法巴尔的摩燃烧的街道时问道,莱维引用了他的话。某种程度上,沃尔夫·布利策这一周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种族隔离使一些问题在被忽视之前变得不可见,直到它们燃烧得太亮,无法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