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是好的:为硅谷辩护 - 彭博社
Joel Stein
萨姆·阿尔特曼坐在他的桌子后面,膝盖抱在胸前,吃着干杏。 他29岁,但即使是最放任自流的酒保也会查他的身份证。 他思考时总是抓着头发,让它像爱因斯坦那样竖起来。 他表示他的主要兴趣确实是物理学,尽管当他进入斯坦福大学时,他主修计算机科学,因为“我已经对物理学了解很多。”他的T恤上写着“做一些人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他所经营的加速器Y Combinator的口号。 作为交换,它提供7%的股权,发放12万美元和三个月的Wi-Fi、咖啡、停车和免费建议给全新的初创公司。 Airbnb和Dropbox是它的一些成功案例。 当被问及为什么人们认为硅谷的科技企业家如此讨厌时,阿尔特曼吃完一个杏子,扭动着手指间的头发,说:“硅谷有大量傲慢的混蛋,这并没有帮助。”
最近,傲慢的混蛋遭到了反击。 在过去的18个月左右,随着抗议者对旧金山的绅士化进行抗议,发生了自由派之间的暴力事件,他们割破轮胎、打破窗户,并且在一个案例中,故意在谷歌和雅虎用来将员工从城市运送到南方40英里处的办公室的私人巴士上呕吐。 在一封致《华尔街日报》的信中,82岁的硅谷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汤姆·帕金斯将这些对1%的攻击比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这种比较并没有提升对话。 至少有两个人在旧金山因被称为“玻璃洞”(即佩戴谷歌备受嘲讽的内置摄像头眼镜)而遭到攻击。 当98岁的玛丽·伊丽莎白·菲利普斯自1937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旧金山时,面临驱逐,抗议者蜂拥而至,指责购买她公寓大楼的房地产公司,认为科技资金(和房东的贪婪)是她的处境的原因。 2010年1月,旧金山的失业率为10.1%,在市长李孟贤提供激励措施让科技企业留在城市后;现在失业率降至4.4%,并推动公司迁往奥克兰,那里失业率从17.6%降至8.9%,而咖啡师的失业率则更低。 这些问题并不是世界大多数人会反对的,但即使是积极的破坏也会造成负面的“外部性”,正如帕洛阿尔托人可能会说的那样。 在四月,抗议者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组织在一位37岁谷歌风险投资合伙人的旧金山家外,张贴带有笑脸的传单,上面写着:
凯文·罗斯是一个寄生虫。……他资助的初创公司带来了那些摧残旧金山和奥克兰土地的企业家们。……我们是那些为他们提供咖啡、送餐、照看孩子和拖地的人。
迈克·贾德,一位曾经的工程师,创作了电视系列剧 比维斯与巴特海德 和 山丘之王 以及电影 办公室空间 和 愚蠢的乌托邦,制作了HBO的情景喜剧 硅谷,它讽刺了工程师的完全优越态度。“直到最近,占领华尔街的人似乎并没有对史蒂夫·乔布斯或科技界感到愤怒。尽管那就是0.001%的人的生活,”他说。占领硅谷已经开始。
这些抗议大多与住房成本和收入不平等有关。它们还涉及美国是否在二十多岁的程序员身上投入了过多的资源,这些程序员制作智能手机应用,以及是否给予这些家伙过多的信任,让他们处理电子邮件、网络搜索和个人照片。脸书上个月遭受打击,因为它透露对不知情的用户进行了心理实验;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因向联邦政府提供信息而受到抨击(尽管许多公司拒绝并被法院命令这样做)。谷歌的形象更糟糕:巨大的黑窗巴士;与国家安全局的合作;装有旋转摄像头的“老大哥”汽车为谷歌地球收集“街景”;收购波士顿动力公司,该公司制造的军事机器人不禁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的警示故事;“不作恶”的口号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它们是否真的在做恶的问题。
考虑到在黑客大会上对“Titstare”应用程序的热烈掌声,该应用程序允许男性分享他们盯着胸部的照片,以及Snapchat联合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在斯坦福大学兄弟会时泄露的性别歧视电子邮件,似乎复仇的极客可能对女性的态度比运动员更糟。简而言之,人们在想,这些不断向我们保证他们正在改变世界的奋斗者,实际上是否完全是混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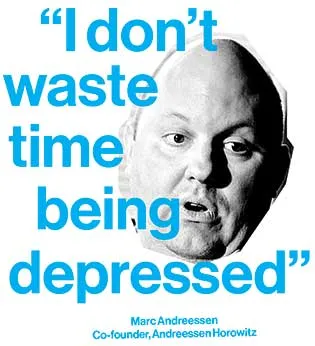 照片由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提供
照片由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提供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市场对智能手机上的无聊事物给予了过高的回报。“当你看到人们做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改变世界……人们真的很讨厌那种情况。这是一种特殊的傲慢,”阿特曼说,他指出在Y Combinator中几乎不给公司创始人任何一般建议,除了“不要过度承诺”和“不要成为傲慢的创始人”。他补充说,当Yo,一个只是在手机上发布“yo”这个词的应用程序,在7月获得150万美元的融资,估值达到1000万美元时,很难让人们不质疑整个硅谷。这就是为什么他用自己的钱主要投资于能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人们觉得我们非常幸运,应该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工作,”他说。
如果Yo容易被嘲笑,它也并不是那么具有代表性。往往,当硅谷的初创公司自夸他们正在做一些成熟企业和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时,他们是对的。当政府与汽车公司谈判以调整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时,埃隆·马斯克已经制造出每个人都想要的电动跑车。那项要求汽车公司从2016年开始逐步安装倒车摄像头的法律可能每年拯救69条生命;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尚未造成碰撞。Uber是解决酒后驾驶问题比公共服务公告更实际的解决方案。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140字符文本的地图,大家分享他们正在吃的东西,将改变世界,他们在Twitter成为组织塔赫里尔广场抗议活动的主要工具之前,似乎是傻瓜。根据BBC和其他新闻媒体的报道,8月份,以色列人开始使用Yo相互警告火箭袭击。 无论是否傲慢,硅谷仍然引领着经济。旧式的美国乐观主义在湾区仍然是规则,移民受到欢迎,努力工作得到回报,每个人都相信他们的孩子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比斯马克·莱佩,34岁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5岁时帮助他的墨西哥移民农民父母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德采草莓,创办了Ooyala(在线视频)和Wizeline(产品管理)。他说,关于硅谷精神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史蒂夫·乔布斯1997年的苹果广告中:
向那些疯狂的人致敬……那些以不同方式看待事物的人。他们不喜欢规则。并且他们对现状毫无尊重。你可以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赞美或诋毁他们。但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忽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因为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正是那些真正做到的人。
“你真的可以把‘疯狂’换成‘傲慢’,”Lepe说。“因为你必须傲慢才能改变世界。”  摄影: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在星期二,Y Combinator的创业创始人聚集在一起 吃晚餐和听演讲;最近的两位演讲者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在这些晚上,加速器的山景城办公室看起来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咖啡馆——二十多个年轻男士和三位女性佩戴着名牌,在一系列长桌上用便宜的折叠椅打字。橙色的墙壁上覆盖着泡沫隔音材料,这在程序员制造噪音的情况下是有意义的。由于加速器不进行第二轮投资,创始人在小组会议中可以自由承认自己的不足,这些会议感觉有点像治疗会议。在七月的一次会议上,很快就清楚技术傲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合作伙伴、投资者和招聘者的面子。一个家伙叹气,承认他无法找到一种方法让用户在他的网站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取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其他人试图用一些方法来安慰他,想出一些可能让他们上当的办法。他们都感叹有规定阻止他让人们送药,并建议他去一些购物中心问问年长女性她们服用什么奇怪的非处方药。如果这些正在接受培训的世界改变者对破坏的危害不敏感,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自己的生活:从其他城镇或国家搬来,拒绝高薪工作以接受低薪,住在办公室,并且至少隐约意识到他们的业务几乎肯定会失败。
摄影: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在星期二,Y Combinator的创业创始人聚集在一起 吃晚餐和听演讲;最近的两位演讲者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在这些晚上,加速器的山景城办公室看起来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咖啡馆——二十多个年轻男士和三位女性佩戴着名牌,在一系列长桌上用便宜的折叠椅打字。橙色的墙壁上覆盖着泡沫隔音材料,这在程序员制造噪音的情况下是有意义的。由于加速器不进行第二轮投资,创始人在小组会议中可以自由承认自己的不足,这些会议感觉有点像治疗会议。在七月的一次会议上,很快就清楚技术傲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合作伙伴、投资者和招聘者的面子。一个家伙叹气,承认他无法找到一种方法让用户在他的网站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取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其他人试图用一些方法来安慰他,想出一些可能让他们上当的办法。他们都感叹有规定阻止他让人们送药,并建议他去一些购物中心问问年长女性她们服用什么奇怪的非处方药。如果这些正在接受培训的世界改变者对破坏的危害不敏感,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自己的生活:从其他城镇或国家搬来,拒绝高薪工作以接受低薪,住在办公室,并且至少隐约意识到他们的业务几乎肯定会失败。
他们坐在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和他的狗的肖像下,这幅画最初是劳伦·鲍威尔·乔布斯(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送的生日礼物。康威很快拒绝了它,现在它已成为一种俗气的物品——象征着硅谷的伦理与东海岸的格格不入。表现得像个自满的富人并不是一种正确的傲慢。真正酷的是如果有人用油画描绘你的精彩代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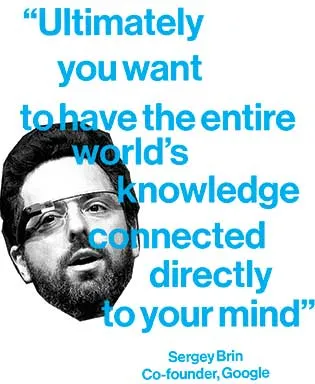 摄影: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
摄影: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
阿尔特曼和大多数硅谷的人一样,穿着打扮得像还是中学生。Y Combinator资助了他的公司Loopt,这是一家与Foursquare竞争的公司,让人们可以与朋友分享他们的位置。他在2005年辍学于斯坦福大学后创办了Loopt,并在2012年以434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自从获得这笔意外之财后,他买了一些酷炫的汽车(工程师通常喜欢汽车),但他仍然和两个兄弟在旧金山租住一间公寓,喝着他在斯坦福宿舍里用的同款宜家玻璃杯。几年前,他终于买了一个床架,因为他放在地板上的床垫漏水后长出了惊人的霉菌。“在纽约和洛杉矶等大多数城市,人们重视短期现金或补偿。但在硅谷,有很多延迟投资,这样才能建立公司,”他说。“在纽约,人们有压力要在汉普顿买房或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里的高地位并不是开一辆超级豪华的车或拥有一栋大房子或新衣服,而是进行天使投资。风险越大,越好。”是的,他们对彼此公司的估值非常痴迷,但这也是他们竞争激烈的打分方式。当人们嘲笑斯皮格尔拒绝了来自Facebook的30亿美元时,他们并不理解他并不想要更多的钱;他想要建立和控制一家庞大而有影响力的公司。大多数硅谷企业家并不是为了致富而创业。他们的雄心远不止于此。
迈克·弗朗戈,23岁,作为纽约花旗集团的债券交易员,目睹了大量的消费和喧嚣。他来到Y Combinator,想要创建一个网站,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以便他们可以购买对冲基金的小份额。“华尔街不关心什么是对的,”他说。“他们关心什么是合法的。在这里,他们关心什么是对的。”即使科技高管夸大了他们改变世界的能力,这难道不是比拉斯维加斯的Cosmopolitan酒店的瓶装服务更好的目标吗?
 摄影: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
摄影: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
这从一开始就是硅谷的DNA。在1999年CNN的一部特别节目中,探讨了互联网泡沫的兴奋与奢华,风险投资家史蒂夫·朱尔维森挑战了该节目的假设,即硅谷是西海岸的华尔街。“认为有人会说‘我只是为了钱’几乎是犯罪的。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想改变世界,”他说。7月通过电话联系时,朱尔维森认为硅谷的目标没有改变;如果有的话,变得更加宏伟。“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全球思考,关注贫富差距或医疗保健,”他说。“他们不考虑奥巴马医保,因为那太小了。他们忽视现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创造这个新的MOOC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你只需忽视一切陷入政府泥潭的东西,创造一个新系统。”
达娜·林格曼,36岁,在旧金山的SoMa区的砖墙办公室里运营众筹网站Indiegogo,那里一面墙上挂着吉他,另一面墙上排列着员工的自行车,还有一面墙在一次涂鸦课上被装饰过。电梯附近的灯光上写着“赋权”这个词。她把脚放在一个巨型吊灯下的桌子上,脚上有一个因在挪威的夜间人行道摔倒而打上的石膏。作为一个罕见的旧金山本地人,她戴着厚边眼镜,长长的金发中分。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陷入困境的搬家公司,在她上大学时宣告破产。她上了一所私立高中(凭奖学金),数学课通常意味着围坐在一个圈子里讨论数学问题。本月晚些时候,她将参加迪帕克·乔普拉的智者与科学家研讨会。
通过Indiegogo,她试图为每一个有价值想法的人筹集资金,包括缺乏商业雄心的艺术家。为远离硅谷的人们提供资金,多少有些讽刺,使她的这家非常硅谷的公司变得庞大。“我爸爸总是告诉我,世界不喜欢变化,”林格曼说。“它喜欢说不。它并不是想要邪恶。它只是不了解。作为企业家,你的工作就是与之抗争。他们会为你所做的感到高兴。但不要指望他们会感谢你。商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善良来源。它可能是最好的善良来源。”在硅谷,即使是嬉皮士听起来也像安·兰德。
 摄影:帕特里克·T·法伦/彭博社
摄影:帕特里克·T·法伦/彭博社
劳伦斯·莱西格,一位作者和哈佛法学院教授,创立了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他认为西海岸的代码(编程)与东海岸的代码(法律)存在冲突。今年早些时候,他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花费1200万美元为希望废除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候选人做广告。莱西格表示,本世纪头十年技术领袖的初步自由主义倾向已被与政府打交道的实际挫败感所取代。“有一个雅虎工程师,真是个天才,他跟我谈论他的拍卖理论研究,”他说。“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才能在医疗保健或社会保障方面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说,‘我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处理药品定价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想法,他们不让我进去。’”他说,美国在资源配置政府方面的方式如此落后,以至于无法利用新颖的想法。
在HealthTap,这家位于帕洛阿尔托大学大道的初创公司允许用户与当地医生进行视频聊天以进行评估,创始人罗恩·古特曼,41岁,对改善世界的决心更加坚定。“在面试中,如果他们不谈论想要做好事和产生影响,我们就不会雇佣他们。无论他们多么优秀,这就是面试过程的结束,”他说。他放下冰绿茶,走到办公室楼上的前面,在木制站立式办公桌、佛像和盆栽花卉前,开始他的每周全公司会议。这里的掌声比排球比赛还要多。当我被介绍时,他们为我鼓掌。当我说你好时,他们再次鼓掌。“我们推出HealthTap的那一天,世界将会改变。它会改变,”他说,伴随着掌声。在会议结束时,人们必须谈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如何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相关。然后所有50名员工一起做波浪动作。
古特曼有改变世界的主张。超过14,000人给他写了电子邮件,表示他的应用程序拯救了他们的生命。而且,几乎没有人会不同意他的使命声明:“我认为医疗保健是人权。我认为政府在提供这一权利方面做得很糟糕,”他说。作为一名以色列移民,古特曼每天午餐都吃来自附近外卖店Sprout Café的同样沙拉。他说他不在自己的网站上投放广告,放弃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因为这会影响他的内容。“如果我有很多钱,我能吃多少个Sprout的沙拉?”他问。“‘改变世界’是硅谷中被滥用的三个词。但我的人生使命是以非常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世界。”  摄影: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除了金钱,迅速膨胀科技创始人自尊心的另一件事是获得资金的机会。**自然,批评者迅速指出这些机会似乎偏向一个熟悉的人口群体:白人男性。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
摄影: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除了金钱,迅速膨胀科技创始人自尊心的另一件事是获得资金的机会。**自然,批评者迅速指出这些机会似乎偏向一个熟悉的人口群体:白人男性。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
是的,科技企业家绝大多数是男性,进入这一领域的女性越来越少。2012年,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占18%;而在1985年,这一比例为37%。但她们并不全是白人;硅谷的初创公司中充满了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巴基斯坦人——还有一些WASP。
“白人是融入的委婉说法,”Glimpse的联合创始人埃莉萨·谢文斯基解释道,Glimpse是一款Snapchat竞争对手,允许用户发送迅速消失的照片和视频。谢文斯基在纽约皇后区与单身母亲一起长大,并在公立学校上学。当她第一次找工作时,她说:“我尽量减少让我显得与众不同的方式。我只是顺应那些笑话。我感觉我没有选择。笑话中有太多色情笑话。甚至在代码中也内置了。”当她申请加速器的资金时,为了不让人们对她的性别感到紧张,她写道:“我发现我有一个24岁男孩的幽默感。”
Shevinsky说,她遇到的少数人是“兄弟程序员”——那些喝酒如命的麻省理工学院兄弟会成员,他们的约会观念是让波士顿大学的女性乘车来参加派对——但兄弟程序员文化足够主导,以至于在TechCrunch Disrupt SF黑客马拉松上,有两个家伙展示了Titstare应用。Shevinsky在她的商业伙伴为Titstare辩护后辞去了Glimpse的职务。他道歉了,她回来了,新的头衔是“女老板”。
对于在硅谷工作的女性,Shevinsky表示,情况正在慢慢改善。Y Combinator的董事会现在有四位女性合伙人,并举办一个名为女性创始人会议的活动,而谷歌和推特对缺乏女性和少数族裔员工的透明度(谷歌70%男性,91%白人和亚裔;推特70%和88%)正在使科技公司更加关注多样性。但担心这些问题并不是硅谷的自然状态。“这里有一种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允许很多事情发生,”Shevinsky说。“我第一位创业律师告诉我,初创公司是人力资源灾难。它们违反了很多法律,而这些都被忽视了。这是件好事,因为否则那些公司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
硅谷也有自己的政治。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立场有时发生冲突——小政府与枪支管制、帮助穷人、放松行业监管——这并不困扰大多数人,因为他们很少考虑政治。当他们考虑时,通常是为了证明谁更政治正确。Mozilla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Brendan Eich在四月被发现曾在2008年支持加州的反同性婚姻提案捐赠了1000美元。他被迫辞职。这在快餐鸡肉行业是不会发生的。
硅谷极端自由主义的一方曾谈论过将硅谷变成自己的州(这是201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真正的投票提案,由风险投资家 蒂姆·德雷珀提出);通过在美国边界外创建浮动城市进行海上定居(一个实际的机构正在研究这个,得到了来自彼得·蒂尔的50万美元捐款);在游轮上设立办公室以规避移民法(Blueseed,一家承诺提供900万美元资金的公司);以及创建一个拥有自己虚拟法律的虚拟世界(这是风险投资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的提案,他来自安德森·霍洛维茨,而彭博社则是其投资者之一)。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帕特里克·弗里德曼正在研究海上定居计划,他说:“硅谷的做事方式显著优于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方法。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政府并不是自负。我们有这些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府,而它们在21世纪表现不佳。政府具备了一个准备被颠覆的行业的所有特征。” 在最近的一个星期五晚上,29岁的Box联合创始人亚伦·莱维展示了他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庞大办公室,员工超过1000人。莱维通过在手上写字来做笔记,在华盛顿州的梅瑟岛高中时因为他的犹太卷发和狂热的精力被称为“尖叫”。莱维表示,他正在与其他首席执行官讨论如何以更非正式的方式与政府监管机构互动。这是一场斗争——监管者似乎不理解最新的技术。当他走动时,他逐个叫出每位员工的名字,询问他们是否在做什么酷的事情。他们没有,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热情。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黄色螺旋滑梯,乒乓球的声音,以及一个告诉客人用密码“Q2MakeM0mPr0ud!”登录免费Wi-Fi的标志。莱维在办公室里住了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女友,一位公共利益律师,要求他买一张床。“有床没有任何用处。组装一个宜家家具需要太多时间,”他说。“我们仍然没有空调。我们得打电话找人。”
Levie 已加入 Salesforce.com 首席执行官 Marc Benioff 的 SF Gives,这是一个为当地慈善机构筹集的 1200 万美元基金,Benioff 在谷歌公交抗议开始后 60 天内从科技公司筹集了这笔资金。Salesforce.com 在旧金山拥有超过 5000 名员工,他们占用了近 150 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我们可能是问题的最大例子,但感谢上帝,没有人把我们当作问题来指责,”Benioff 说。作为第四代旧金山人,他的祖父创建了湾区快速交通系统,他表示,他认为 Salesforce 已经与抗议活动隔离,因为它将 1% 的股权、利润和员工时间捐赠给当地慈善机构。“我们的员工在辅导他们的孩子,当他们去医院时,我们的员工会在那里迎接他们,”他说。“我们的员工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里。所以我们在外面有一些好的因果关系。”
Erin McElroy 赞同这一观点。这位 31 岁的活动家自学编程,创建了反驱逐映射项目,展示了旧金山的所有驱逐情况并列出了房东。“我并不是说我对 Salesforce 没有批评,”她说。“但我们抗议谷歌、苹果、脸书等公司的原因,而不是 Salesforce,这有其原因。”
Benioff 已捐赠 2 亿美元用于资助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儿童医院,他将 SF Gives 的 1200 万美元交给了慈善家和前 Levi Strauss 首席执行官 Peter Haas 的继子 Daniel Lurie。Lurie 经营 Tipping Point,这是一个为当地慈善机构提供风险投资的公司;他向他认为能提供最大帮助的非营利组织捐赠 25 万美元。Lurie 办公室的一部分被用于新的 T Lab 孵化器,九位“问题解决者”获得资助,花六个月时间探索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早期儿童教育和囚犯重新融入社会的解决方案。
尽管硅谷有大量年轻的自由主义富豪,但它仍然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并可能会给予更多。麦克艾尔罗伊说,问题在于这些大额捐款——以及许多科技公司——在湾区的好处有限。“他们仍然与当地脱节,”她说。“这关乎改变远方人们的生活,这与这种新殖民主义有关。人们对他们的企业在这里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多意识。谷歌和苹果正在将资金外包,并在其他地方剥削人。”
汤姆·普雷斯顿-维尔纳在哈维·穆德学院读了两年后辍学,2004年创立了Gravatar,随后将其出售,并建立了GitHub,允许程序员分享和存储代码。2012年,安德森-霍洛维茨以7.5亿美元的估值投资了1亿美元;办公室里有一个酒吧,一个DJ,以及一个完整的椭圆形办公室复制品,总统印章被“GitHub联合精英”所取代。今年四月,普雷斯顿-维尔纳因前员工朱莉·安·霍瓦斯对公司性别歧视和恐吓的指控而辞职。(GitHub的调查未发现任何法律不当行为;普雷斯顿-维尔纳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承认“错误”,并在一篇博客中道歉。)
自从离开GitHub后,他和妻子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为CoderDojo非营利编程俱乐部的贫困儿童提供200美元的Chromebook。“也许他们会解决其他问题,而不是另一个图片分享网站,”他在位于他公寓附近的Fiore Caffé喝咖啡时说,那里是旧金山绅士化的中心。普雷斯顿-维尔纳留着时髦的胡须,慢慢而认真地说:“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其他问题:他们的教育糟糕透顶;他们可能有卫生问题。”他担心未来硅谷会变得更加强大,而其他地方的国家将被抛在后面。“在未来,可能会有两种类型的工作:一种是你告诉机器该做什么,编程计算机,另一种是机器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他说。“你要么是创造自动化的人,要么就是被自动化。”这与凯文·罗斯公寓楼外那个笑脸传单上写的内容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