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主义如何让城市失望(以及可能如何重振它们) - 彭博社
bloom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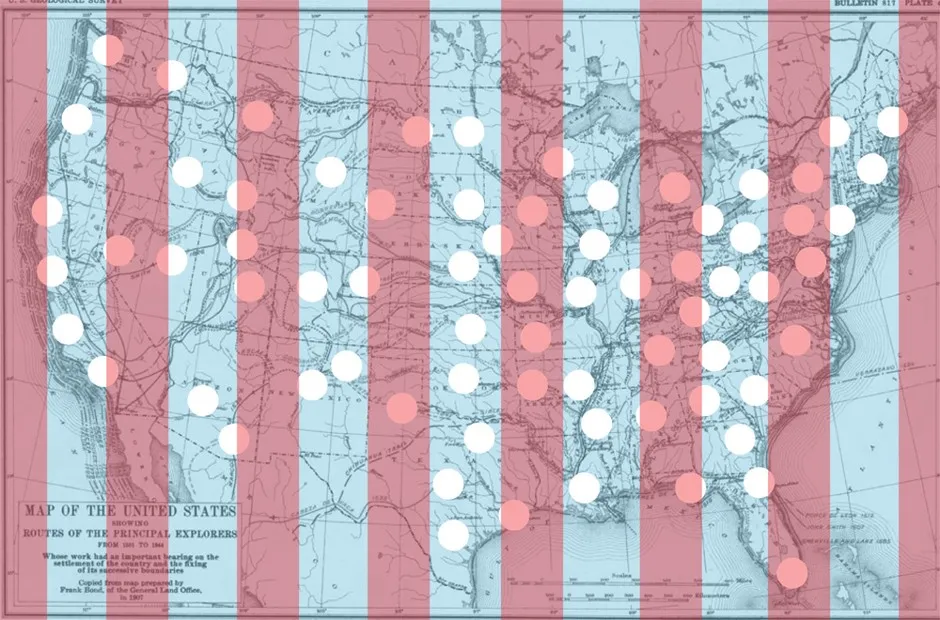 马克·伯恩斯美国的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引擎和我们的贸易与投资中心。它们提供并帮助资助我们国家的公共产品,并通过多种权力影响我们建成环境的形状、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因此,影响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个人和职业生活。
马克·伯恩斯美国的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引擎和我们的贸易与投资中心。它们提供并帮助资助我们国家的公共产品,并通过多种权力影响我们建成环境的形状、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因此,影响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个人和职业生活。
然而,城市和大都市地区不能独自应对。它们的努力依赖于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尽管它们可能令人恼火、干涉和专横。州和联邦政府通过强制性权利、税收激励和支出计划,成为城市和大都市地区、其基础设施、居民(特别是弱势居民)以及其前沿机构的最大单一投资者。它们设定了城市和大都市(及其公司和核心机构)发展先进产业、吸引全球人才和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的游戏规则。
是时候认识到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是行动者,而不是受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州和联邦政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层次、出于不同的目的——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经济基础设施(例如,高等教育机构、先进研究机构、大型医疗综合体)、物理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水和污水)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学校、支持服务)方面都是大型的共同投资者。无法想象硅谷、研究三角区或波士顿大都市区在20世纪末的“知识城市”崛起,而不承认联邦在基础和应用科学方面的投资以及州对公立大学的投资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同样,低估国家安全网对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经济演变的积极影响也是危险的。人本导向和地方导向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良性的交集。联邦和州对老年人和非常贫困者、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持减轻了城市和大都市地区——以及它们的私人和公民慈善机构——必须承担的补充收入和提供服务的财政负担。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贝尔法斯特的中央车站为北爱尔兰的公共交通创造了新时代芝加哥应该考虑所有解决预算危机的方案,普利兹克说消除美国道路死亡的月球计划AOC提议300亿美元的社会住房管理局与此同时,州和联邦在城市的行动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早在1969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教授(后来成为尼克松总统的城市事务顾问,最终成为一位强大的美国参议员)就解释道: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政府的部门或机构,其项目不会以某种方式对城市的生活及其居民产生重要影响。通常——人们不禁想说是正常的!——相关的政治任命者和职业高管似乎并不认为自己与其项目和政策的城市后果有关,更不用说负责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建造高速公路、担保抵押贷款、推动农业,或者其他什么。没有人明确告诉他们,他们同时在重新分配就业机会、隔离或去隔离社区、使乡村人口减少并填满贫民窟等:所有这些都是名义上无关的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后果。
莫伊尼汉描述了联邦和州政府如何将专业知识神圣化,并将自己组织成一系列由不同立法委员会监督的分散的执行机构。各州不仅利用其权力来定义和限制城市和市政当局的权力和地理范围,还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常常滑稽的特殊目的实体:学区、消防区、图书馆区、污水区、蚊子区、公共利益公司、工业发展局、交通局、港务局、劳动力投资委员会、重建局、控制委员会和紧急财务经理。根本上,城市和大都市地区要么是被施加影响的地方,要么是州和联邦干预的背景和地点,无论是好是坏。它们被视为一个可以被忽视(或偶尔安抚)的选民群体,而不是在自身权利上塑造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城市被视为一个被忽视的选民群体,而不是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时候认识到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是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对象。我们知道如何谈论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联邦主义,这是一种安排,各州将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但保留其他权力,以便不同层级的政府作为双重主权行使权力。但大都市在这一构架中显得格外缺失。它们在美国宪法中没有位置,并且在州法中缺席,州法承认市镇、村庄、城市、乡镇和县,但不承认它们所属于的大都市地区。大都市并不是由单一的行政首长治理,而是通过商业、公共、慈善、非营利和民选领导者的重叠网络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在政治上权力较小,但在经济上比各州更强大。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同的经济时代。现在被青睐的生产系统是灵活和分散的,而不是标准化和集中的。生产的关键因素现在是创新和知识,而不是资本和劳动。经济变革的浪潮使城市和大都市在应对新基本面方面处于前沿:知识交流、创新者网络、合作的重要性上升,以及地方中介机构和平台的中心地位,包括大都市本身。
最能服务于推动21世纪经济发展的城市和大都市的联邦主义,不是传统的“双重主权”,即根据主题划分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力,而是一种为设定优先事项和领导实施的城市和大都市服务的协作联邦主义*。*这需要重新排序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关注宪法主权者——州和联邦政府——如何与其城市和大都市合作伙伴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互动,共同创造公共利益。
每个大都市地区及其领导网络都可以轻松地每年举办几次与代表该大都市的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构的人员的会议。这些“都市党团”可以成为一个两党合作、商业化的工具,用于跟踪大都市产生的愿景和倡议,以及可以为之服务的联邦和州政策及投资。这些会议应该是动手实践的工作会议,提供一个联邦主义的等价物,以解决城市和大都市领导者在基层所遵循的问题解决过程。一些来自大城市(如纽约)的联邦代表团确实有作为党团会议的传统。这些党团会议应该由大都市主导,并包括州(或多个州)和联邦代表团,以便这两个主权能够共同解决问题,以及与他们在城市和大都市层面的公共和私人合作伙伴网络一起。
经济变革的浪潮使城市处于应对新经济基本面的前沿。除了这种定期的互动和合作外,大都市地区最需要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是相当简单的,尽管很少被讨论。首先,大都市领导者需要联邦和州政府为国家脆弱和弱势公民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安全网和一个进步的税收系统。这意味着在国家增长、多样化和老龄化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权利项目(并进行改进和提高效率)。这还意味着,考虑到更广泛的工资动态,通过在联邦和州层面明智地投资于诸如所得税抵免和可退还儿童税抵免等权利项目,使工作获得报酬。但仅仅明智地投资于人是不够的。税法必须公平,以便贫困公民不会因通过累退的州销售税等方式为政府服务融资而承担不当负担。
其次,大都市需要州和联邦政府支持他们试图建立的经济。许多商业、大学和慈善领袖一直主张政府进一步投资于创新、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增强美国在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总统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由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担任主席——建议公共和私人研发投资在2020年前增加到美国GDP的至少3%,以便美国保持其作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像费利克斯·罗哈滕这样的受人尊敬的商业领袖一直是国家基础设施银行的坚定支持者,该银行将利用公共资源来撬动私营部门资本进行广泛的必要投资。道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利维里斯呼吁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以及社区学院的技能培训项目上进行重大投资,以便工人能够学习在美国高薪先进制造业工作所需的技能。
联邦政府还有一个关键任务:为了帮助像波特兰和迈阿密这样的城市领导者进一步国际化美国经济,国会和总统需要在移民改革、优惠贸易协议以及对外国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的新开放政策上采取行动。美国的多样性和孤立性同时存在,使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国家不同。我们的都市地区在参与和受益于商品、服务、思想、资本和人员的无缝交流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洛杉矶并不制定移民规则,波特兰也不确定贸易和投资的框架,迈阿密也不决定影响商业竞争的反垄断法。这些决定必须在国家或州级别作出,以创建共同市场和共同规则,否则在大都市规模上将会出现混乱。大都市的权力并不免除联邦和州政府在增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方面采取强有力、明确的行动。无所作为的后果是进一步限制大都市的全球化并抑制大都市的表现。如果美国的大都市要完全具备全球流利性,他们的共同主权者需要为全球参与铺平道路。
这里提到的所有事情都超出了传统城市政策的范围。这应该是这样。联邦政府没有“州”政策。将重要事项限制在联邦政府的小分支和角落里是荒谬的,因为现代挑战的多维特性以及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多层次、交织的关系。但这正是美国对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所做的。自1965年以来,我们就有了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尽管对城市和大都市(以及住房)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在政府的其他地方制定的。回想一下联邦政府(和各州)如何参与那些重大、改变游戏规则的倡议:与移民、研究与发展、早期教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没有人会称这些为“城市”政策。它们并没有占用联邦预算中的一小部分,就像社区发展区块拨款或其他典型的“城市”项目一样。城市政策再也无法包含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力量,即使它曾经能够。
这篇文章改编自大都市革命,现已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